
《如诗的地毯:喀布尔男孩成长记》
在喀布尔的街头巷尾,
一个男孩的梦,轻轻飘荡。
他的名字叫阿里,
在纷繁的世界中,编织希望。
晨曦初露,阳光洒在尘土上,
阿里的小手,在地毯上舞动。
每一针,每一线,
都是他对未来的憧憬。
地毯上,波斯图案绽放,
如同喀布尔的古老传说,
每一朵花,每一片叶,
都讲述着阿里心中的故事。
战争的风暴,曾席卷这片土地,
阿里看着家园破碎,泪水涟涟。
但他没有放弃,他的心依然坚韧,
在逆境中,他学会了坚强。
他拾起破碎的碎片,
用爱和汗水,重新拼接。
每一块,都是他的勇气,
每一块,都是他的成长。
喀布尔的孩子们,
在硝烟中,寻找着快乐。
阿里带着他的小弟弟,
在街头巷尾,追逐嬉戏。
地毯的图案,越来越精致,
阿里的心,也越来越宽广。
他学会了分享,学会了爱,
学会了在苦难中,寻找光明。
岁月流转,阿里长大了,
他成为了地毯的传承者。
他的手艺,如同诗篇,
将喀布尔的美丽,传递四方。
如诗的地毯,铺满了世界,
阿里的故事,传遍了天涯。
他的成长,是一部史诗,
在喀布尔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相关内容:

「我现年二十九岁,大学毕业,拥有自己的地毯事业,有时会和外国人打交道。我四肢健全,这在地雷充斥的阿富汗可不是容易的事。我出身良好家庭,至今未婚。我是普什图人,但有双哈札拉人的眼睛」这是一个阿富汗男孩成长与辛苦求生的真实故事。
凯斯?阿克巴?欧马小时候,当年的喀布尔美丽得像一座大花园;在祖父的大宅里,凯斯与堂兄一起在屋顶上放风筝,他的父母、叔叔婶婶会围坐在草地上喝茶,讲故事,念诗,卖地毯,并忙着撮合婚事。
「在战火、炮弹、军阀和他们虚假的承诺之前,在我们熟悉的人物无端从人间消亡或流亡异乡之前,在塔利班和他们疯狂的行径之前,在空气还未弥漫死亡气息之前,在大地尚未沾染红色鲜血之前——我们原本生活美满。」(〈花园里的麦金塔〉)
1980年代末,当俄罗斯人撤离後,凯斯以为会看到蹬着亮鋥鋥军靴的英雄到来,结果来的却是一群脏兮兮像大贼般的圣战士。内战爆发,他们所住的邻里成了冲突的前线,欧马家族放弃一切,逃到一山之隔的九塔堡避难。
「『听我说。我们也许再没机会说话了。若这些人让你非常难受,你可能会认为自杀是摆脱所有悲伤最好的办法,但是你要相信我,那绝对行不通。』祖父语气严厉而果断,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这样说话??『你必须当个勇敢的孩子,若他们真的要杀你,张开双臂拥抱死亡,绝对不要乞怜求生,因为到头来,死亡终究会找上我们。』」(〈漫长回家路〉)
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後,凯斯的父亲决定带着孩子出国,开启一段险象环生的旅程:他们曾蜷伏栖身在巴米扬大佛後面的岩洞,遇上巨石洪水与猛兽;亦曾避居於过着游牧生活的表亲家,加入传统牧人的行列。凯斯在这段旅程中渐渐长大,并认识一位善织地毯的神秘少女,让他理解自己在世上的意义与目的。
「这个世界永远不缺花草树木。一物死了,另一物必取而代之。自创世以来,事情就是如此。世界和万物就像玫瑰花苞,一开始都是紧闭着,等待温暖的春风吹拂。我们必须随时都像温暖的春风,让每种花的花苞都绽放。」(〈寄居在大佛的头里〉)
後来,圣战士退场,改由疯狂的塔利班上台,阿富汗人学会无声的抵抗。凯斯熬过残酷与不分青红皂白的监禁,十八岁时悄悄开了一家地下地毯工厂,冒死提供邻居女孩工作机会,并为家人带来离开阿富汗的希望。只是当美国九一一事件发生後,他们的命运再次出现逆转??
「怪事一件接着一件发生,我们这下懂了,我们现在过的是与恶魔为伍的生活,却假装自己过的是正常日子,唯有这样,才能让自己苟延残喘地活下去。我不知道该怎麽开始这『崭新』的人生。每天醒来,一吐一纳之间,只能坐着等生活出现改变。这下我了解到,等待是一门必须精通的绝技。我告诉自己,往者已逝,现在必须做些全新尝试。但是每天我的心彷佛困在笼子里,被过去的记忆重重压着。」(〈金子〉)
在这本精彩的回忆录里,凯斯重述了派系斗争时生命的朝不保夕、塔利班掌权时日子变得如何荒诞不仁,阿富汗人民在各方蹂躏下依旧不放弃对生存的渴望。本书如传说般曲折,如诗歌般优美,见证了可战胜一切的顽强生命力。
摘文精选
1花园里的麦金塔
在战火、炮弹、军阀和他们虚假的承诺之前,在我们熟悉的人物无端从人间消亡或流亡异乡之前,在塔利班和他们疯狂的行径之前,在空气还未弥漫死亡气息之前,在大地尚未沾染红色鲜血之前——我们原本生活美满。
我们没有保留照片,在塔利班执政期间,这麽做太危险了,因此我们把照片都销毁。但是绝望降临阿富汗之前,我们对昔日的生活点滴依旧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印象。
母亲穿着短裙,坐在银行的办公室里,服务大排长龙的客户。她在银行受到大家敬重,一来是因为她娴熟银行业务,二来是因为她有能力解决客户问题。
父亲穿着喇叭裤,骑着摩托车驰骋於喀布尔的大街小巷,那模样简直就像个电影明星。有时他会用一条皮带把我紧紧绑在背後,看着他的长发迎风飞扬。他在转角咻地转弯时,两腿上的金属护膝因为摩擦人行道而冒出火花。隔天我把这告诉同班同学,大家都歆羡不已。
我有个叔叔因为做生意经常飞往国外。其他叔叔与婶婶在喀布尔念大学,大家都非常讲究时尚。祖父将一头浓密的白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身上的西装是义大利手工量身订做,高雅又显贵气。每次他一现身,都是全场的焦点。
祖父人高马大,虎背宽肩。不同於多数阿富汗人,他会将古铜色脸庞上的胡子刮得乾乾净净。最让人过目难忘的,是他又大又黑的双眼,如此的深邃、慑人,如此的温柔。
这些画面会突然涌现,有时发生在极为普通的场景。
父亲叫着我的名字,要我准备上学。我张开双眼,看了一下床头墙上的钟,时间还早,但我能对父亲抱怨吗?他是我父亲,我是他儿子。普什图族的儿子必须对父亲言听计从。
但我真的还想睡个回笼觉。我揉着惺忪的双眼,听着父亲持续喊道:「起床了!戴上手套,我在拳击场等你。」他希望我能在早饭前和他一起运动。他已经开始对我进行体能训练,希望我能和他一样当个知名的拳击手,参加各大国际比赛。
我讨厌早起,但是我喜欢和父亲一起运动。他每次都放水让我赢,尽管我只有七岁。
我也喜欢上学,从不跷课缺席。我不仅聪明,而且人缘好。有时同学会向校长抱怨,说我欺负他们,戳他们的脸。但是校长会罩我,因为他是祖父最好的朋友。但是校长从不对我笑。
我和大我一岁半的姊姊念同一所学校。她比我聪明,也比我会做人。尽管她是鼎鼎有名拳击手的女儿,但她从不欺负女同学。
祖父的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
祖父在一九六○年代末盖了这间房子,当时他在阿富汗国家银行(Bank-e-Millie)担任会计专员。那时正值阿富汗经济起飞,祖父预见沿着喀布尔河而建的千年蜿蜒肠径,将容纳不下日益壮大的喀布尔。
於是他买下远在陡峭小山另一头约五英亩的土地,该山的双峰数百年来屏障了喀布尔的南边与西边。当时那块土地以外的地方全是农地,土砖搭盖的村落散见其间,但这光景并未维持太久。
祖父购地前做了一番研究,并和熟悉该地的农民交换意见,最後小心翼翼选中这块拥有一口好井的地。即使碰上一连几个月的旱季,邻居可能缺水,但我们一家仍有水可用。祖父在自有地的四周盖起固若金汤的水泥墙,但保留一部分地兴建学校,让附近孩子能够上学,他知道这些小孩的家庭不久将变卖农地,改建成住宅区。
父亲有七个兄弟,他和其他六兄弟、六兄弟的老婆以及小孩,全都安居於祖父盖的大宅里。我有超过二十五个堂兄弟,大家年纪相仿,会一起玩乐。每个叔伯的家都有单独的两间大房,栉比鳞次地排列在花园一端的单层楼房里。祖父的住房在花园的另一边。老中两代隔着花园,花园里种了六十棵麦金塔苹果树,树苗是祖父的堂兄从美国携回,经过和阿富汗品种的苹果树接枝改造,成了阿富汗非常稀有的品种,祖父对此引以为傲。
紧临大宅外有一排三层楼公寓,一楼是店面,二、三楼是住家。祖父将公寓出租给非亲非故的人。公寓的窗户全面向街道,阿富汗人不会让陌生人往内窥探自家的院子。
父亲在其中一个店面开了健身房,每天放学後,数十名年轻男子会在这里受训,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拳击手。堂兄瓦基尔(Wakeel)和我会站在人行道看着他们对着沙包练拳、做伏地挺身、跳绳,父亲则在拳击台上和一个或两个人格斗。
瓦基尔大我七岁,是我梦寐以求却永不可得的兄长(我是家里长男),而我也是他梦寐以求的弟弟。我模仿学员练拳时,他充当我的沙包。每次打到他时,他都笑笑地回应。
祖父当时已从银行退休,将其中一个稍大的店面拿来充当存放地毯的仓库。仓库的门又厚又重,并套上一把牢不可破的锁,里面充满着从羊毯溢出的羊毛脂香甜的气味。祖父在仓库摆放了数千条地毯,堂兄弟和我喜欢在堆高的地毯丛中跳来跳去。
所有叔伯都有自己的事业,但瓦基尔的父亲例外,他在阿富汗的国防军服役,官拜少校。他老爱说:「做生意风险太大,多数生意人都有心脏病,或是早死。」他是祖父的长子,因此在家中地位特殊,他和老婆、儿子瓦基尔(我最喜欢的堂兄)以及两个女儿靠着军饷过着舒适悠哉的生活。
某天他去了办公室,自此音讯杳然。我们至今不知道他是生是死。当时我第一次听到「共产主义」这个词,但不知道那是什麽意思。如今二十五个年头过去了,婶婶还是痴痴地等着他回家,直到现在每当有人敲门,她就立刻奔到门边一探究竟。
父亲是祖父的第三个儿子,像所有其他兄弟一样,只娶一个老婆。我们家族不时兴三妻四妾。
邻居把父亲视为圣人,对他非常尊敬。他们来找父亲,和他讨论生意以及碰到的难题。尽管他们有些人的年纪比父亲还大,但他们会称父亲为拉拉(Lala),意为「老大哥」。他们跟父亲说:「你的想法比你的年纪还老成。」父亲勇於尝试一切,「不」这个字,对他完全派不上用场。
他也是唯一接手祖父地毯事业的儿子。他的五个弟弟认为地毯已成过去式,应该放眼未来,靠崭新方式赚钱。
其中一个叔叔从俄罗斯进口产品,另外两个叔叔还在念大学,但考虑进口医药卖给阿富汗全国药局。
通常我们会一起用晚餐,有超过五十人坐在庭院的一角,大家拿着座垫围成一圈,中间有块布铺在祖父精心修剪的草坪上,彩色小灯泡悬挂在头上。晚餐後,祖父与儿子们聚拢来谈论生意与事业,或是讨论该送我以及其他堂兄弟去美国还是欧洲哪间大学留学。
妇女们则围坐在另一边,讨论家务事。年纪较长的妇女得负责替年纪较小的女孩(例如父亲有两个尚未出嫁的妹妹)找个好丈夫。这两个单身的姑姑和我们住在一起。至於父亲的两个姊姊已经出嫁,并搬去和夫家同住,她们的夫家也在喀布尔,但不在同一区。所有家族成员都会参与讨论谁是合适的人选,而且一谈就是好几个月。
和我同辈的堂兄弟姊妹则围坐在另一圈,大家比赛说鬼故事,或是欣赏喀布尔明朗的夜空,看着月亮与星星高挂天际。大家若听腻了故事,就对着星星想像动物的形状,然後开心大笑。
吃完晚餐,有时候父亲或是其中一个叔叔会带着我们小孩绕山一圈,在诺城公园(Shahr-e-NawPark)附近购买冰淇淋,或是到电影院看一出印度或是美国电影。
喀布尔当年有如一座大花园,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形成一条绿色隧道。市区里到处是受到妥善打理的公园,里面高大的粉红色蜀葵、亮橘的金盏花、万紫千红的玫瑰花在互相争奇斗艳。家家户户都有花园,种着石榴、杏仁、杏树等等。就连市郊那座有着双峰的陡峭小山每逢春雨时节,山顶也会被低矮灌木丛或绿草所覆盖。在春季与秋季,往返於俄罗斯西伯利亚大草原与印度之间的水鸟凌空而过,栖息在喀布尔四周的湿地。古老的地下水道将山泉引到市区,让家家户户的花园永保常绿。
到了每周五穆斯林假日,学校停课,店家休市,我们一家人会准备丰盛的午餐到附近的花园散心,或是在卡尔加湖(QarghaLake)附近、帕格曼山谷(PaghmanValley)内野餐,甚至远至萨朗隘口(SalangPass),隘口位於兴都库什山(HinduKush)的高海拔处,距离喀布尔以北开车约一小时。周五是大家族成员聚会、互访、互开玩笑、闲聊八卦的日子。
堂兄弟和我会去爬山,那些长辈则靠着大型枕,躺在柳树或是桐树的树盖下休息。其他人一杯接着一杯地喝茶,未婚的姑姑们就忙着煮水泡茶。在长长的午後,大家轮流把芝麻蒜皮小事拿出来加油添醋,逗得大家开心大笑。当然,大家想方设法要说得比另一人精彩,毕竟我们是阿富汗人。我母亲是当中的佼佼者。
叔叔们演奏塔布拉鼓(tabla),父亲吹奏木笛,不过父亲从未接受正规训练。我们唱歌、跳舞、烤食物,一直待到天色已深才回家。
有时家族外出郊游时,堂兄弟姊妹会进行课业比赛,谁拿最高分,就可以要求其他堂亲出钱买他们想要的东西,价格无上限。大家竞争得非常激烈,我们父母充当裁判,每次我们答对,爸妈都高声叫好。有时比赛不分胜负,平手收场。我们都讨厌这样的结果。
偶尔有些堂亲会因此而吵架,冷战一两天,但多半维持不久,因为禁不起一起玩的诱惑。不管是在花园里躲猫猫、打弹珠,在附近公园比赛谁骑的脚踏车比较快,抑或是在屋顶上放风筝,都让我们小孩玩得乐不思蜀,没完没了。
每个春季与秋季的下午当微风吹起,数百个风筝升空,将喀布尔的天空挤得「水泄不通」,直到天幕变黑为止。放风筝不只是游戏,还牵涉到个人的自尊,若能成功磨断对手的风筝线,可是一件引以为傲的事。技巧在於利用速度与拉力,缠住然後割断对手的风筝线。
瓦基尔是放风筝的高手,也是我们大家的指导老师。因为他割断太多人的风筝线,所以街坊小孩给他冠了个头衔──「狠心断线手瓦基尔」。
某天下午,瓦基尔和我拿着风筝走上屋顶时,对着我说:「我们来比赛!」一如既往,他乌黑的长发披垂在额头轻拂着双眉,浓眉下深邃的双眼闪闪发光。永远都是如此。
我说好。尽管我知道他准是赢家,但是就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赢不了,也不可以不接战帖,我们自小就被教导不可以逃避奋战。
祖父建造的出租公寓的顶楼平台是斗风筝的理想地点。不仅高於街道两旁的路树,更像是个表演舞台。在平地的观众(大人小孩皆有)看到风筝升空,会一一放下手边的工作,抬头观看比赛结果。一场精彩比赛将成为大家接下来数天谈论的话题。
我们两人的风筝在空中缠斗了约半小时,瓦基尔在顶楼遥远的另一端惊讶地喊道:「你进步得真快!以前我只消五分钟就能让你断线,现在已撑过了半个多小时,你的风筝还继续停留在空中。」
突然他耍了一计我从未见过的高招,让风筝绕着我的打转,彷佛要「掐死」它,我感到手中的风筝线一松,眼睁睁看着风筝垂死,像片秋叶在空中飘荡,离我愈来愈远。
瓦基尔露出灿笑,得意洋洋地让风筝飞得更高,用以向街上观众炫耀他又斗赢了。我跑下楼,赶紧拿来另外一个风筝。
比拉(Berar)是哈札拉人,年纪约十多岁,是我们家园丁的帮手。他热爱斗风筝,每次我和瓦基尔比赛,他都一脸羡慕,目不转睛地盯着交锋的风筝。
比拉大瓦基尔几岁,人长得又高又英俊,工作态度认真。他的家人住在巴米扬(Bamyan),那里有大佛的佛像刻在山壁上。比拉并非他的真名,比拉在哈札拉语的意思是「兄弟」,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名,他也不介意我们叫他比拉。
瓦基尔和我还分不出胜负之际,比拉忍不住一直盯着天空。老园丁不耐地念了他几次。「你该看的是地上的杂草,而非天空。」园丁对比拉一向不假辞色。
「让那小夥子休息一下。」祖父对园丁道。园丁和比拉正在打理祖父心爱的玫瑰花丛。刚好我又对天空放了另一只风筝,祖父对比拉点头道:「去吧。」
比拉跑上屋顶,看到我正奋力地让风筝爬到高点,避开瓦基尔的奇袭。比拉从我的手中抢走风筝线,并叫我握紧线轴。
我从未看过比拉放风筝。我一直对他喊道:「加油!加油!用力拉!」但比拉根本不需我的指点,他精准地知道该怎麽做。瓦基尔大声对我吼道,就算我有一百个帮手,他还是会割断我的风筝线。瓦基尔又高又瘦,不过他很壮,用力地扯着他的风筝,让风筝绕着我的打转。
比拉让风筝飞得又高又快,很快就高於瓦基尔的风筝,然後他让风筝俯冲,速度之快彷佛石头从天而降。瓦基尔的风筝突然断了线,於空中失速载浮载沉、左右飘荡,逐渐远离瓦基尔手上残余的风筝线,朝坎达哈的方向飞去。
我爬上比拉的肩膀,高兴地尖叫,并抓牢风筝线,让风筝飞得更高,宛若一只小小鸟。街坊邻居的小孩也跟着叫好,他们并未看到比拉斗风筝的技巧,只看到在比拉厚实肩膀上的我,兴奋地喊道:「瓦基尔,狠心断线手被断线了!」我亲了比拉数次,他是我的英雄。他给了我「断线手的杀手」这个头衔,尽管那都是他的功劳。
瓦基尔生气了,两天不跟我说话。
我另外一个仅比我小几个月的堂弟,人缘极差,跟谁都处不来,瓦基尔动不动就叫他傻B,其他堂兄弟也跟着喊他「傻B」。
他若添购新衣,一定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然後说些蠢话。「我们去了那间几周前在诺城开幕的新店,那里贩售从伦敦与巴黎进口的高档货。店家跟我父母说我对衣服的品味出众。我想你们这些家伙应该买不起我身上这件西装。」我问他售价时,他把价格灌水了三倍。
瓦基尔问他:「嘿,傻B,那麽贵的衣服会耍魔法吗?」
傻B就是傻B,永远不知道人家在开他玩笑,反而中计地问了一些没大脑的问题,诸如:「什麽魔法?」
「它们可以让你变帅,看起来没那麽丑吗?」瓦基尔道,然後便纵声大笑。
我们也跟着大笑,气得傻B跑回家,找父母投诉。为了躲避大人惩罚,我们会跑到屋顶、庭院或躲在父亲停在车库的汽车里。
每次傻B穿上好衣服到处炫耀时,瓦基尔就喝上满口的水,我呢就揍他肚子一拳,他噗嗤一声,将水一古脑喷到傻B身上,傻B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们,怒气冲冲地质问我们,为什麽要这样作弄他。
瓦基尔告诉他:「这是一种锻链,好让自己更强悍。我们出其不意的对彼此出拳,以後若和谁打架,才不会吃亏。你也应该把自己锻链得又强又悍。」然後我们出拳猛揍他肚子,但刻意避开他的脸,以免留下瘀青,否则被他父母看到,我和瓦基尔恐怕逃不了一顿挨打。
傻B有个跌破大家眼镜的长处:他酷爱阅读。他的知识远超出他这个年纪应该知道的,而且记忆力过人。也因为这样,我们更想欺负他。
我们堂兄弟在家一起玩时,瓦基尔老爱找傻B的碴,但是出了家门,瓦基尔绝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他。瓦基尔彷佛我们的大哥哥,每次傻B和邻家男孩打架(这事经常发生),瓦基尔一定挺身保护他。在公园踢足球时,瓦基尔每次都要傻B和我跟他同一组,这样他才能罩我们。
我们的街坊邻居安静温和,跟我们相似,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附近人家一有婚宴或订婚派对,所有邻居都会受邀参加,并带着孩子与仆役赴会。
每周五在清真寺结束祷告後,祖父会发言十分钟,和邻居讨论如何保持社区清洁、如何解决水电问题、如何打理公园,还有如何兴建更多设施让小孩有地方一起嬉戏。他从未出马竞选什麽官职,但大家对他言听计从。
若有某户人家的财务出了问题,这家的长者会私下来找祖父,希望能获得邻居们的帮忙。然後,周五祷告结束时,祖父会在清真寺向其他男士表示,有人需要一些钱,但绝不透露是谁,因为重要的是保护这家人的颜面与尊严。
某个周五,其他人都离开了清真寺,我看到祖父把刚筹到的钱交给一个邻居,他的妻子已生病数月。男子亲吻祖父的双手,说道:「你从来没让我们失望,愿真主保佑你长寿、身强、体健。」祖父发现我在看他,皱眉看我一眼,脸露不悦,我立刻转身跑开,因为这是我不该看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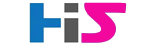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