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小帽《我的日本爸爸》、出版社/究竟出版
于是,我有了个日本爸爸
我对亲生父亲的感情说不上恨或讨厌,比较多的反而是陌生和无感。对我而言,这段关係是需要和解的,只是我还没有準备好,因为不想逼自己背着道德期望,让自己觉得要和解,所以我静待水到渠成的一天。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不常在家,但是我知道他在外面有很多不同的。我永远记得母亲告诉我要和父亲离婚的时候,她来徵询我的意见,我二话不说就回答。我对父亲的印象,很多来自童年的相本,长大后回去看那些照片:在万里海滩、在儿童乐园、在大同水上乐园……才想起原来我有去过那些地方;从照片中才得知:喔~原来我爸也在。
那些曾让我母亲以泪洗面的阿姨,我记得的只有一个,后来阿姨跟我爸生了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从母姓。阿姨没有对我不好,不过若要叫,我也叫不出口就是了。
我记得在父母离婚前,父亲带我去过一间位于现在的市民大道、微风广场对面的小套房,也就是很有名的诊所楼上,当年还没有市民大道,从基隆经台北南下的火车,铁道还会经过那间小套房所在的华厦,去了才知道,那是父亲和阿姨一起住的地方。
中学后,父母已经离婚,他和阿姨顺理成章地有了另外的家,母亲对我去见父亲一事,态度一向都很大方,还会三不五时催我:所以学生时代后期,我反转了童年贫穷的命运,因为幸运的话,有些月分我可以获得两份零用钱。
出社会工作之后,很怕接到父亲的电话,因为通常是来跟我要钱的。这通电话会有一道公式:先问候我近况如何、身体好不好,要我好好照顾自己……然后就準备进入重点。早期薪水较少、每个月收入和支出几乎打平的时候,他开口要个三、五千元对我来说其实是种负担;薪水好一点的时候,变成给得起、但内心有些不甘:母亲从小养我到大,没开口跟我要过一分钱,而你……怎么可以?
还有一种难过是,每一次打电话的目的都是为了钱。因为有目的性,所以目的说出口前的对话都是铺陈、都是暖身、都让我觉得假装。所以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好怕看到来电者是的显示。
这个词,在我的人生里就是一个血缘所衍生的称谓。就算是欧吉桑,我也从来不觉得因为母亲再婚嫁给他,他就填补了这个空洞,过去二、三十年,他在我眼中就是我母亲的伴侣、一个我称为的叔叔。
这段时间,即便将他从病恹恹照顾到身体康复,却发现过去我经常自己去买便当的餐厅,步行距离对我来说轻而易举,但欧吉桑从家里到目的地的过程要停下来休息很多次。
有一次,我们去一间牛排馆,搭公车只有一站的距离,但他途中停下来四次,若坐公车,牛排馆在对面,又刚好在两个红绿灯路口的中间,所以我们必须走一个字型到对面,真的是让我进退两难。
有个週末傍晚,我福至心灵拿起翻译软体问他:他说。于是我们就一起骑着车,他从后方抱着我,我边骑、一路上边跟他介绍:这间是涮涮锅、这间咖啡,日本也有、这间是卖日式汉堡排……想带着母亲到处走、到处玩、到处吃的心愿,如今移植到欧吉桑身上来了。不敢相信!日本爸爸就这样真的闯进了我的生活。
前篇提到帮他办手机门号,其实也是希望他可以,也应该更接近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要再因为语言隔阂,过得像个旅客,希望他有落地生根的感受。
于是,我有了个日本爸爸。

最后一次旅行
我相信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中自有安排。
母亲在日本居住的二十多年间,我最常去旅游的国家就是日本;而这一生,我仅有带着她和欧吉桑从台湾出发到海外旅游的经验,之后伴随而来的,都是生命给予我的迎头痛击:第一次去澳门,住顶级的酒店、欣赏太阳剧团表演……旅行结束后的半年后,她被诊断出罹患肺腺癌。
另一次是我陪她和欧吉桑一起回东京,那趟旅程从松山机场起飞后就惊险万分,最后虽然平安返抵国门,她却在三个多月后去当了天使。如果能够早点知道那是我们母子的最后一次出游,我对她的耐性会多一点、说话的口气会好一些,就像我如果能知道那年平安夜的急诊住院,已经是她生命的倒数计时,那一个月我会放下所有工作和私人生活,把时间全都留给她。
可惜千金难买早知道。
二○一六年十月,我计画一个人到大阪玩,母亲也差不多在那时间要和欧吉桑回东京办事情,原本我打算先去大阪几天,再搭新干线去东京和他们会合,但讨论之后觉得行程太赶、太麻烦,最后我放弃大阪,和两老一起从台北出发。我很庆幸当时做了这样的决定,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我根本不敢想像,少了我,他们该怎么办?
母亲那时已经不太能够走路,双腿水肿无力,每走一小段路就会喘个不停。我们向地勤人员请求协助,办完check in与托运行李后,有专人带领我们一路通关,畅行无阻到飞机顺利起飞。
刚开始,母亲还跟我有说有笑,但随着飞行高度不断攀升,她开始变得不太对劲,原本出游的兴奋感渐渐被焦虑的神色取代,她呼吸变得急促,告诉我:
那一刻我慌了,欧吉桑也很着急,连忙按了服务铃请空服员帮忙,空姐大概也没遇过这样的情况,机上虽然有急救设备,拿来却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赶紧再找来其他同事协助,一群人手忙脚乱……而我们才刚起飞不久,距离日本的飞行时间还要两个小时。
最后,空姐为母亲戴上呼吸器,打开氧气瓶顺利供氧,总算缓解她的不适。那个时期,母亲还有一个问题:频尿。严格来说应该是排尿不顺,很容易有尿意,辛苦走到厕所后却不容易解尿,反而经常在从马桶起身时,因为腹部用力,压迫到膀胱时,尿液外流而弄湿裤子。她在飞机上戴着氧气面罩,但不时想起身上厕所,明明已经举步维艰,我告诉她既然已经穿了纸尿裤,就不要让自己那么辛苦,先尿在纸尿裤里就好,但她是个非常爱乾净的人,坚持要去上洗手间,所以在那趟飞行过程中,我就陪着她起身、上厕所、失败、回座、再起身、再艰辛地走去厕所……反覆来回好几趟。
她好折腾,我好心疼。
两小时过去,我们总算平安抵达羽田机场,虽然全程提心吊胆、紧张到我的衣服早已湿透,但当脚踏出登机门、踩在空桥地板上的那一刻,我终于鬆了一口气。同时也担心,一週后的回程会不会要再经历一次?光想就头痛。
取行李、出关,搭车来到饭店,一路上我还是神经紧绷,下车后,我先跟饭店借轮椅。这两位老人为了省钱,选了家便宜的饭店,门口没有无障碍设施,反而有三段小阶梯,不高就是了。我问母亲:她说可以,但是当她试图从轮椅起身时,忽然一个腿软,我赶紧从腋下接住她,最后还是让她坐回轮椅,我和欧吉桑将她扛进 Lobby(那时候,欧吉桑还很健壮)。
我直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母亲的状况这么差?如果是肿瘤压迫到肺部、喘个不停,这我可以理解;但是双腿无力、神智恍惚,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甲状腺亢进造成的?但是她明明有在吃药啊!
一进房间,我将她先安顿好,马上想找药给她吃、帮她把气管扩张剂拿出来,结果她又来了!上一秒躺下,下一秒钟又想上厕所。我扶着她走到浴室门口,这该死的设计,浴室竟然是架高的,而且高度还不低。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荒谬、折磨、能摧毁我意志的考验,都在这天下午发生了。万万没想到,最惊悚的还在后头,当我打开母亲的药盒,翻遍行李箱里所有的药袋,却看不到她的甲亢药。
我问:
母亲气若游丝地说:
我气急败坏地说:我傻了,无言以对,她该不会每天吃的甲亢药,就是我买给她补充体力的维他命?
我真的傻眼。
一种懊恼、惊吓、生气、不知所措的複杂情绪涌上心头,气母亲怎么会连自己吃什么药都不知道、收行李的时候欧吉桑没有帮忙检查吗?更气自己怎么如此疏忽、不尽责,没有想过母亲有可能会带错药、吃错药。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发抖,因为当下我非常恐惧跟担心:她的身子每下愈况,该不会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正确服药了?
我力持镇定。一边深呼吸,一边跟自己说要冷静,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这是我一贯的做事方式。眼前最困难的是语言不通,我们一家三口平常的沟通方式,都是母亲居中翻译,此时此刻翻译机秀逗了,谁来帮帮我们?
我疯狂打电话。找懂日文的同事帮忙翻译,请她把母亲的状况告诉欧吉桑,要他赶快找医院;同时也在FB发出求救讯号:有没有正在日本念书的台湾友人,愿意过来帮忙?也打电话回家,告诉家人关于母亲的情形,请他们上楼翻一下她在家里的药袋,看看还有哪些药品?并且到处问人,有没有人刚好明天要来东京,能充当人肉快递,帮我把母亲需要的药带过来?再不行,我买张机票请人专程帮我送药来!
所谓的照顾
母亲从平安夜送急诊、住进加护病房到离开这个世界,短短三十八天。从确诊肺腺癌到过世的六年间,她历经手术、化疗、转移、再手术、再化疗……一路上都很配合跟勇敢,但我和她一直有个共识,若真的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我必须放手让她走,不要让她承受无谓的痛苦。
多年后回想,母亲生命最后的那一个多月,情况真的很差,呼吸器几乎拿不下来,全脸式的氧气面罩在她脸上勒出痕迹,没有力气吃喝,令我非常心疼。临别那一天,我才刚从医院回到家,又被看护的电话call回去,说医师跟护理师正在抢救,希望帮我们争取更多时间,让家人能够及时赶到。
欧吉桑和母亲的姊姊(犹如我第二母亲的阿姨)、哥哥、姊姊和姪甥们陆续赶到,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几个闺密也来见母亲最后一面,她们都和母亲很熟。在那当下,我的心非常混乱、害怕,但我记得大家围在床边,都是请母亲安心地离开;我握着母亲的手,头靠在她的脸庞,彷彿回到小时候跟她撒娇的光景。
我依稀听到嫂嫂还是姊姊跟母亲说:欧吉桑听不懂周围的人在说什么,只是不断拿着手帕拭泪,那是我从十几岁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看到他在哭。最后,我在母亲的耳边跟她说:接着,仪器上的心律,就像电影中看到的那样,慢慢变成一条线……
自那一刻起,我没有母亲了。
母亲在世时,看过我工作平步青云,成就最值得她骄傲的阶段,有时候我会庆幸她离开的时间点刚刚好,因为在那之后的几年,媒体生态转变更为剧烈,而我也历经北漂、失意返台、返台失业、失业后重新再站起来的人生震荡,这些起伏,就不需要让她看见而徒增担心了。
我一直很想去看看大陆市场,但前二十年的记者生涯,採访工作做得顺风顺水,加上母亲在跟病魔抗战,就算有欧吉桑陪伴,我还是不可能抛下她去远方;她生病的这六年,我最自豪的是她每一次从基隆到台大回诊、打针化疗,我没有一次缺席,领到了全勤奖—虽然这张奖状,未能帮我留住母亲。
她离开之后,我没有家累、没有牵绊了,所以想去对岸闯一闯。
从小我就是一个非常能自理的孩子,小至染髮、穿耳洞、大到联考只选传播系以及买房子,都是做了决定之后才告诉母亲,而她也总是支持着我。
所以当以前的老闆、葛福鸿(葛姊)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到北京工作,我听到合作对象是当红的艺人,又争取到不错的薪资福利,没有犹豫多久就义无反顾地去了(至于北漂的故事,又有许多说不完的篇章)。
那么,欧吉桑呢?说好的照顾呢?
母亲在世时,我每两个礼拜会回基隆一趟;母亲离开后,我一年回基隆两趟。我的家庭背景是这样:父母离异后,我跟着母亲生活;后来她去日本工作赚钱,也因此遇到欧吉桑。我的成长过程几乎是阿姨、姨丈一家在照顾我,感情的亲密程度,是我从来不会叫哥哥、姊姊为表哥、表姊。
阿姨视我如己出,兄姊们就像我的亲手足,所以后来母亲有能力买房子,我们两家就买在同一幢楼的楼上楼下,互为照应、互相照顾。
当时的我认为,因为跟欧吉桑的语言不通,回家得面对鸡同鸭讲的境况,为了避免尴尬,决定减少回基隆的次数。所以去北京打拚,对他来说应该没差吧?每个月我还是会準时把生活费转帐到他的户头,让他一个人在台湾仍能吃、住无虞,这就是当下我认为的照顾了。

风云变色的单身生活
记忆中,在我小时候,家是很的。房子是租的,善良的奶奶被倒会欠了很多钱,父亲常常不在家,为了生活,母亲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在朋友介绍下赴日本工作;我小学毕业前,她就和我父亲离婚了,之后的二十多年她长住日本,每年回来一、两次,或是我在寒暑假时飞过去探亲。
母亲上班的地方是一家台湾人开的、可以喝酒和唱卡拉OK的店,其实我没有真正问过她工作内容,但大概像《华灯初上》里的Rose妈妈、Sue妈妈那样吧?(还是其实是百合?总不可能是阿季吧,喂~)
母亲个头娇小如白冰冰,牡羊座的她个性刚烈,年轻时的一双大眼很像金马影后惠英红,豪迈的歌声宛如ØZI的妈妈叶瑷菱。
她外型漂亮有女人味,豪爽的个性又不输男人,所以异性缘一直很好。在我中学阶段,同时有三、四个不同的在追求她,但高中毕业之前,就被淘汰到只剩一位,不知道他用什么打动了母亲,还是母亲什么特质吸引他,总之他们从此只为彼此转身,他就是现在成为我继父的欧吉桑。
因为语言上的隔阂,多数时间我和欧吉桑没有什么互动,但我很清楚并感激,在成长的路上他给予我的资助与供养:每一回去日本玩或出差,都是他和母亲开车来机场接送;我去日本就像回家,白天工作、逛街,回到家里他会準备生鱼片、河豚火锅、和牛寿喜烧……冰箱打开,永远有最大颗的苹果和水蜜桃。
退休后,他和母亲一起搬回台湾生活。当时他看起来还很健朗,完全看不出已快七十岁,母亲差不多六十岁,我心想她大半辈子都在海外生活,晚年心情应该是想落叶归根,而且回来还有儿子可以依靠。我清楚记得当时她说:我说。
但也许真的是因为我和欧吉桑没有血缘关係,所以母亲走之后那几年,虽然我很难过、痛苦,同时又有一种如释重负、这辈子再也不需要为别人生老病死牵挂的轻鬆,也因此才能毅然决然地去北京工作。
欧吉桑有糖尿病,十多年前他第一次被诊断出此病症,是因为连续喝了几天的汽水、果汁,血糖值高到爆表测不到,就像母亲平安夜入院一样,从基隆赶到台北急诊。我在急诊室看到他时大为吃惊,因为他整个人面黄枯瘦、小了一号,颓靡的模样很像快熄灭的蜡烛。经历那一次危机,他戒掉菸酒,饮食变得清淡,持续回诊看医生。
他定时吃药,每三个月回诊,幸运的是,那位新陈代谢科医师刚好会说日文,所以这些年我都自以为安心地把他丢给基隆家人照顾,让姪子开车载他去看病,我在台北、北京过我的生活,从来没有陪他去过一次医院。他确诊Covid–19时,我也是火速帮他张罗隔离期间的食物跟清冠一号,隔着基隆的家门向他说:仅此而已。
二○二二年底,他在基隆的家因低血糖昏迷,三个月内又发生第二次。得知消息的当下,我都在重要的工作与会议中,没有在第一时间面对他倒在地上的冲击画面,打一一九叫救护车的人也不是我。我是在工作空档时,打电话问家人关于他的病情进度:醒了吗?有意识吗?看护来了吗?
有空的时候就去医院看他、买一些吃的,该付的钱我付,该买什么我买,差不多就这样。我知道自己在逃避,因为就算我去了医院,还是没办法跟他沟通,去干嘛呢?还有,自从母亲过世之后,我极度抗拒去任何医院探病,深怕被勾起很多已尘封、不想再浮现的画面。
昏倒了两次,就可能会有第三次,他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
该怎么办呢?我必须想办法。
申请长照?服务人员客气地跟我说,他不是本国籍,无法免费。
送他去住养老院?不可能吧,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被欺负、虐待怎么办?
回日本,也就是他的国家申请安养院?哇!光想到他会有被丢包的感受,我就满满的罪恶感。
至于二十四小时的外籍看护,应该可行,但申请需要时间,绝对赶不及在他出院之前,还有,若他和看护两个人住在基隆,语言不通该怎么解决?
所以我决定把他接来台北自己照顾。
出院那天,问他需不需要轮椅?他说不用,但看他拿着拐杖走路的背影,八十三岁的他已经比六年前母亲离世时苍老、孱弱许多。
自那天起,我和我的日本爸爸,正式开启新同居生活。那也意味,我十多年自在的单身生活,从此风云变色。

这道人生课题
把欧吉桑接来台北住,最初真的是抱持且战且走的心情,认为就是个阶段性任务,等到他左手复原、生活可以自理了,就能让他回基隆,我也就解脱了。
台北的家有两个房间,一大一小,大的是卧房,小的是我的工作室,对于单身的人来说,空间还挺舒适。欧吉桑来到台北的第一晚,睡前我到卧房搬枕头棉被,打算去客厅睡沙发,他说:示意我可以跟他一起睡没关係。
但是我有关係啊!我已经想不起多久没有跟人睡同一张床了,怕对方传出打呼声、怕自己翻身影响别人,所以我宁可睡沙发。从他来的第一天,我每天都在跟上天祈求,保佑他的左手赶快好,可以赶快自己下厨做饭,同时间我也在办理外籍看护申请,希望等一切到位,我的任务就可以告一段落。
除了睡觉,更有关係的事情是:洗澡。出院那天,我问看护小姐:她说:天啊,我真是什么都躲不掉:换药、洗澡、睡沙发。本来还希望看护可以告诉我或之类的答案,但跟据她的形容,真的就是—欧吉桑全身脱光光、左手举高高,扶着墙避免碰到水,让她帮他洗澡。
我家的浴缸很好笑。当初买下这间房,浴缸是一个吸引我的加分项,因为够长、够深,泡脚时双脚可以完全伸直;等我住进来才发现,我家的热水器是储水式的,水放不到浴缸的五分之一,热水器里的热水就没了,要重新再储、再放,所以我住了十多年,只泡过一次澡。但也捨不得拆掉,所以每次洗澡都是在浴缸跨进跨出,挂上浴帘,简单做起乾湿分离。
要帮欧吉桑洗澡,我最担心的是他那双纤瘦的脚出入浴缸会不会很危险、容易滑倒?所以第一次我请他坐在马桶上,就连沖水也是。就算整间浴室的地板会湿掉也无妨,至少比较安全。
第一週,我们,毕竟他都在家,没流什么汗,也尽量减少伤口碰到水的机率。第二次洗澡时,我发现他比较想进浴缸沖水,而且他很贴心,担心莲蓬头的水由高处往下沖会溅到浴缸外头,所以自动蹲下来让我沖水,这对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实在太辛苦了,于是第三次帮他洗澡的那天早上,我去菜市场买了一张矮凳,那天他看我开门抱了张矮凳回家,直接走入浴室,露出会心的微笑。我还帮他戴上塑胶手套(对,就是吃手扒鸡那种),用橡皮筋綑起来,这样伤口沾到水的机率就更低了。

日本人喜欢温泉、泡澡,家家户户都有浴缸,过去我去日本玩,欧吉桑也曾开车载我和母亲到箱根、热海泡汤,我们早在许多大澡堂就裸裎相见过。但跟,完全是两回事。人的一生,除了为人父母帮小孩洗澡之外,帮别人洗澡的机会应该是少之又少吧?
就算他有的,我也有,但看到长辈的重点部位还是挺尴尬。尤其是头一、两次,欧吉桑坐在马桶上,我从站着用沐浴海绵刷洗他的身体,到蹲下来要帮他刷腿时,那么近距离的,感觉真的非常怪异!但我看他还挺自在的,正所谓: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幸好,当我快刷洗到重点部位时,他感受到我的停顿,就把海绵接了过去,完成最后步骤。
照顾欧吉桑,好像是母亲留给我的功课,在她离开后的六年,我被命运指派去面对这份功课,但过程里也意外回放、映照出母亲生前的片段,即便有些画面依然会令我心痛,但就是回来了。
我想起母亲生前,我们三个人最后一次回日本,当时她出入已经需要坐轮椅,但那趟旅行,我们竟还安排了两天一夜的温泉之旅。
下榻饭店的每个房间里都有温泉,但是浴池很深,需要先踩三个石阶才能进到浴缸,以她当时的虚弱程度很容易跌倒,非常危险。
我问母亲:但她害羞不愿意,所以最终我只能妥协,扶着她坐在浴缸的边上,然后开着门、背对着我洗澡,这样我才能放心。夜里,她数度起床尿尿,我也跟着醒来,即便穿着尿布,裤子还是全湿……这些遥远的、不堪的、心痛的回忆,原以为随着母亲化为烟会跟着消逝,却在我和欧吉桑一起生活之后,冷不防地又给我一记回马枪。
在母亲离开、我放飞自己多年后,她丢来这道人生考题,不只是一纸简单的测验,还是三不五时会逼着你複习的考古题。

延伸阅读:
不缺席的爸爸就是最好的礼物!带给孩子稳定与安全感,成为他成长路上重要支柱这样做建立孩子的信心!成长路上大人的陪伴与鼓励,超越考试分数的眼光别再对青春期孩子说!心理师教4招帮孩子建立正确身体意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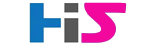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