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87年的深圳,摆地摊就设计衣服,这本身就是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了!在那个改革开放初期、充满无限可能但也资源匮乏、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你能在自己的小摊位上做出能吸引香港老板注意力的设计,这绝对是个了不起的起点。
这听起来像是电影情节,但也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深圳的独特魅力:
1. "敢闯敢试的先锋精神:" 87年的深圳,遍地是机会,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不仅选择来深圳闯荡,还从事设计这种相对需要创意和积累的行业,并且是从摆地摊这种最基层的方式开始,展现了极大的勇气和决心。
2. "设计的潜力与价值:" 你设计的衣服能够吸引香港老板的注意,说明你的设计具有一定的眼光、创意和审美。这在当时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证明内地也能产生有竞争力的设计,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 "时代机遇:" 香港是当时的时尚前沿和国际窗口,香港老板看中内地设计,意味着内地设计开始走向国际视野,或者至少是开始被主流市场所关注。这反映了当时内地与香港之间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内地制造业和设计潜力被逐步发掘的过程。
4. "可能的转折点:" 这次经历很可能成为你人生或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可能为你带来了第一笔订单、第一份合作、第一
相关阅读延伸:87年,我在深圳摆地摊,一个香港老板,看中了我设计的衣服
87年,深圳。
夏天像一口密不透风的蒸锅,把整个东门市场都焖得黏糊糊的。
空气里混着汗味、廉价香水的味道,还有路边牛杂摊飘过来的、带着腥气的香料味。
我叫林蔓,二十岁,从湖南乡下跑到这儿快一年了。
我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方花布铺开的地摊,上面挂着十几件我亲手做的衣服,还有身后那台嘎吱作响的“蝴蝶牌”缝纫机。
这台缝纫机,是我妈传给我的,也是我吃饭的家伙。
旁边摊子的阿娟,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用眼角瞟我。
“阿蔓,又出新款了?你这脑子可真好使。”
她嘴上夸着,眼神里的酸味,隔着三米远都能闻到。
我没理她,低头整理着一件刚做好的蝙蝠衫。的确良的面料,领口用白色丝线绣了一圈小小的栀子花。
这是我熬了两个通宵想出来的花样。
在我们老家,栀子花开的时候,就是女孩子最漂亮的时候。
我想把这份漂亮,卖给深圳的姑娘们。
可深圳的姑娘们,似乎更喜欢那些从香港那边流过来的“水货”。
大垫肩,亮片,紧得能勒死人的牛仔裤。
我的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小清新”,在她们眼里,可能土得掉渣。
一个下午,只开张了一单,卖了条喇叭裤,挣了五块钱。
除去布料成本,净赚三块。
三块钱,够我吃六个馒头,或者一碗不加肉的汤粉。
我心里有点发慌,捏了捏口袋里仅剩的十几块钱。
下个月的摊位费和房租,还不知道在哪儿。
太阳偏西,没那么毒了,人流也渐渐多了起来。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双锃亮的、一尘不染的皮鞋,停在了我的摊位前。
我顺着皮鞋往上看。
白衬衫,西装裤,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表。
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整个人都透着一股“高级”的味道。
是个香港人。
在这里摆摊久了,一眼就能分出来。本地人、外地打工的、香港来的,气场完全不一样。
他没说话,只是弯下腰,拿起我那件绣着栀子花的蝙蝠衫,仔細端详。
他的手指很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不像我,手指上全是针眼和布料磨出来的茧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第一反应是,这人是来找茬的?还是工商局的?
“老板,看看啊?我这衣服都是自己设计的,独一份。”我挤出一个职业假笑。
他没看我,目光依然专注在那件衣服上。
他用手指摩挲着领口的绣花,又翻过来看里面的针脚。
“这花,是你自己绣的?”他开口了,普通话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听起来有点费劲。
“是啊,我妈教我的。”我老实。
“针脚很密,很匀。你学过?”
“没,自己瞎琢磨的。”
他点点头,把衣服放下,又拿起另一件我用牛仔布改的短款夹克。
那夹克上,我用磨砂纸打磨出了几道时髦的“破洞”,还在背上用红线绣了一朵抽象的玫瑰。
他看得更久了。
周围的人来来往往,吵吵嚷嚷,但我们这个小角落,好像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有点快。
“你这些衣服,都是你自己做的?”他终于抬起头,正眼看我。
他的眼神很锐利,像鹰,仿佛能看穿我心里所有的不安和窘迫。
“嗯。”我有点紧张,攥紧了衣角。
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名片夹,抽出一张递给我。
“我叫梁锦成,开服装厂的。”
我愣愣地接过名片。
烫金的字,写着“锦绣服装(香港)有限公司”,下面是他的名字和一串我不认识的繁体字地址,还有一个电话号码。
服装厂老板?
还是香港的?
我脑子有点懵,这幸福来得也太突然了,跟做梦一样。
“你很有天分。”梁锦成说,“但在这里摆地摊,可惜了。”
可惜了。
这三个字,像一根针,轻轻地扎在我心上。
是啊,我也觉得可惜了。
我不想一辈子就守着这个一米见方的地摊,每天为三块五块钱发愁。
我想让更多人穿上我设计的衣服,我想站得更高一点。
“明天上午十点,来这个地址找我。”他指了指名片上的地址,“我们聊聊。”
说完,他没等我,转身就走了。
那双锃亮的皮鞋,很快就汇入了嘈杂的人流,消失不见。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却感觉有千斤重的名片,半天没回过神来。
旁边的阿娟凑了过来,一把抢过我手里的名片。
“哟,香港老板?阿蔓,你这是要走运了啊!”
她啧啧称奇,“小心点,别是骗子。香港老板哪会看得上我们这种地摊货。”
她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从幻想中浇醒。
是啊,骗子。
80年代的深圳,遍地是机会,也遍地是陷阱。
报纸上天天登,说有香港老板骗了厂子,卷钱跑了;还有人被骗去什么模特公司,最后人财两空。
我一个从乡下来的丫头,无亲无故,凭什么能让一个香港大老板看上?
就凭我这几件破衣服?
心里顿时七上八下的。
收了摊,我没舍得坐车,走了四十分钟回到我在上沙村租的农民房。
那是个十几平米的单间,阴暗潮湿,一到下雨天墙壁上就能长出蘑菇来。
我把名片放在桌上,就着昏暗的灯光,翻来覆去地看。
锦绣服装……
听起来像个正经公司的名字。
我给自己下了一碗阳春面,连根青菜都舍不得放。
一边吃,一边想。
去,还是不去?
去,万一是骗子,我连回家的路费都得被骗光。
不去,万一是真的,我可能会错过这辈子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面条在嘴里,一点味道都没有。
我把碗一推,烦躁地站起来。
机会,机会!我来深圳,不就是为了找机会吗?
现在机会送上门了,我倒害怕了?
林蔓啊林蔓,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
我一咬牙,下定了决心。
去!
大不了就是被骗,我烂命一条,身无分文,他能从我身上骗走什么?
第二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
翻箱倒柜,找出我最好的一件衣服。
那是一条我自己做的连衣裙,淡蓝色的棉布,收腰,A字裙摆,领口和袖口都滚了细细的白边。
我觉得这身打扮,至少能让我看起来不那么像个乡下丫头。
我没去出摊,把所有的衣服都锁在柜子里,然后按照名片上的地址,坐上了去南油的公交车。
那是我第一次坐那么久的车,摇摇晃晃,差点吐了。
南油工业区,和我住的上沙村完全是两个世界。
一排排崭新的厂房,高高的烟囱,路上跑着我叫不出名字的货柜车。
空气里都是机器的轰鸣声和一股化学品的气味。
我捏着名片,挨个找门牌号。
最后,在一个挂着“锦绣服装”牌子的大铁门前停了下来。
门口的保安拦住了我,眼神里满是戒备。
“找谁?”
“我找梁锦成,梁老板。”我把名片递过去。
保安打量了我一番,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叽里呱啦说了一通粤语。
过了一会儿,他挂了电话,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梁生在办公室等你,进去吧,左手边第一栋楼,三楼。”
我的心,又开始狂跳。
看来,不是骗子。
我走进厂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巨大的厂房里,几百台缝纫机排得整整齐齐,像等待检阅的士兵。
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服,埋头在机器前飞快地操作着,哒哒哒的声音汇成一片雄壮的交响乐。
空气中弥漫着布料和机油混合的味道。
这,才叫工厂。
我的那个小作坊,跟这里比起来,简直就是个笑话。
我找到了梁锦成的办公室。
他正坐在宽大的老板桌后面,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在看文件。
见我进来,他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坐。”
他的办公室很大,有空调,冷气吹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地上铺着地毯,踩上去软绵绵的。
我局促地坐在沙发边缘,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喝点什么?茶还是汽水?”
“白水就好,谢谢。”
他给我倒了杯水,然后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林小姐,我们开门见山。”他摘下眼镜,“我看过你的设计,很大胆,也很有灵气。”
灵气。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的作品。
“但是,”他话锋一转,“你的做工太粗糙,面料选择也很有问题。只能在地摊上卖,上不了台面。”
他的话很直接,像刀子,但又很中肯。
我无法反驳。
我用的布料,都是从布料市场淘来的便宜货,有时候甚至是些布头。
我的缝纫机,也只是最普通的家用机,锁边都锁不齐。
“我想请你来我的工厂上班。”梁锦成说,“做我的首席设计师。”
首席设计师?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
“我?”我指着自己的鼻子,“可我……我连初中都没毕业,也没正经学过画画。”
“我不需要你的文凭。”梁锦成看着我的眼睛,“我需要的是你的脑子,和你对服装的感觉。”
“我给你开一个月三百块的工资,包吃住。另外,你设计的款式,如果卖得好,我给你销售额的百分之一做提成。”
三百块!
百分之一的提成!
我当时在电子厂打工的姐妹,一个月累死累活,也才一百多块。
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
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一个不真实的、随时会醒的梦。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还是不敢相信。
梁锦成笑了笑,站起身,走到窗边。
“深圳这地方,最不缺的就是工厂和工人。但最缺的,是原创的设计,是能打动人心的东西。”
“我在你的衣服上,看到了那种东西。”
他转过身,“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想好了,就来上班。”
我走出梁锦成的办公室时,腿都是软的。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我还是觉得不真实。
回到出租屋,我把梁锦成的话翻来覆去地想。
首席设计师。
三百块工资。
这几个字,像有魔力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
我几乎没有犹豫。
第二天,我就把地摊上的东西半卖半送地处理了。
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我舍不得卖,找了个角落,用布仔细地盖好。
然后,我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再次走进了锦绣服装厂的大门。
我的新生活,开始了。
工厂给我安排的宿舍,是四人一间,比我之前住的农民房强多了。
有独立的卫生间,还有一个小阳台。
同宿舍的三个女孩,都是车间的女工,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
她们大概都听说了,老板请来一个摆地摊的,当什么“设计师”。
在这个以“计件”论英雄的工厂里,我这个不踩缝纫机却能拿固定高薪的人,无疑是个异类。
梁锦成给了我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就在他的办公室隔壁。
里面有一张巨大的画图桌,还有各种我见都没见过的画图工具和服装设计类的书籍。
那些书,大多是香港台湾出版的,繁体字,配着精美的图片。
我像掉进米缸的老鼠,每天抱着那些书啃。
看不懂的字,就查字典。
梁锦成没有催我马上出设计稿,他说:“你先看,先学。把基础打好。”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看书,画画,去车间里转悠。
车间的主任叫钟叔,是个五十多岁的上海人,技术一流,但脾气又臭又硬。
他看我的眼神,比那些女工更不屑。
“小丫头片子,懂什么叫‘唛架’吗?懂什么叫‘纸样’吗?”
他叼着烟,斜着眼看我,“设计可不是在纸上画几笔那么简单。你画的线,工人做不出来,那就是一张废纸。”
我被他呛得满脸通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因为他说的是事实。
我的脑子里有很多想法,但怎么把这些想法,变成一件可以批量生产的成衣,我一窍不通。
那段时间,我成了钟叔的跟屁虫。
他去哪儿,我去哪儿。
他开会,我就在旁边站着听。他裁剪,我就在旁边看。他骂人,我也在旁边听着。
一开始他很烦我,老是轰我走。
“去去去,小姑娘家家的,别在这儿碍手碍脚。”
我也不说话,就默默地给他递剪刀,扫地上的布屑。
时间长了,他大概也觉得我这人虽然笨,但还算勤快,也就不怎么赶我了。
有时候,他还会主动跟我说几句。
“这个地方,要留‘缝头’,不然缝起来尺寸就不对了。”
“牛仔布要用石磨洗水,才能变软,颜色才好看。”
……
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我拿个小本子,他说一句,我记一句。
晚上回到宿舍,再把这些笔记整理一遍。
宿舍的女孩们都睡了,我还在台灯下画图。
画了撕,撕了又画。
我设计的第一个系列,是牛仔。
因为我在钟叔那里学到了“洗水”的技术,我很兴奋,想立刻实践。
我设计了一款高腰牛仔裤,一款牛仔背带裙,还有一件短款的牛仔夹克。
为了让它们看起来不那么普通,我在裤腿上绣了小小的蒲公英,在背带裙的口袋上拼贴了格子布,在夹克的袖口翻出来是碎花的里衬。
我把设计稿拿给梁锦成看。
他看了很久,点点头。
“有点意思。但是,还不够。”
“不够?”我有点不服气,“哪里不够?”
“不够大胆。”他说,“深圳的年轻人,想要的是最新的,最潮的。你这个,太‘乖’了。”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香港的时尚杂志,递给我。
“看看这个。”
杂志上,一个女明星穿着一件宽大得像麻袋一样的西装,垫肩高高耸起,下面是一条紧身健美裤,踩着一双尖头高跟鞋。
那种夸张的、充满力量感的风格,让我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原来,衣服还可以这样穿。
梁锦成说:“我们的对手,不是深圳的这些小厂,而是香港的品牌。我们要做,就要做能引领潮流的东西。”
引领潮流。
这四个字,让我热血沸腾。
我把原来的设计稿全部推翻,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一个星期。
我画了无数的草图。
我把垫肩加到了衬衫上,把裤腿设计成夸张的萝卜形,我用最大胆的撞色……
最后,我设计出了一款蝙蝠袖的套头衫。
宽松的版型,巨大的袖子,像蝙蝠的翅膀。我用了当时最大胆的宝蓝色和玫红色的拼接。
我觉得,这件衣服,穿在身上,肯定像一只骄傲的孔雀。
当我把这张设计稿放在梁锦成和钟叔面前时,钟叔的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
“这……这是什么玩意儿?”他指着图纸,“袖子比身子还宽,这怎么穿啊?浪费布料!”
梁锦成却盯着图纸,眼睛里在放光。
“好!就做这个!”
钟叔急了:“梁生,你可想好了!这种奇装异服,谁会买啊?做出来卖不掉,我们喝西北风啊?”
“我信她。”梁锦成看着我,语气坚定,“钟叔,打版吧。用最好的料子。”
钟叔气得吹胡子瞪眼,但老板发话了,他也没办法。
打版的过程,异常艰难。
因为蝙蝠袖的剪裁很特殊,稍微有点差错,整个衣服的版型就全毁了。
钟叔带着两个最得力的徒弟,在版房里研究了两天两夜,才勉强做出第一件样衣。
当那件宝蓝拼玫红的蝙蝠衫,穿在假人模特身上时,整个版房的人都安静了。
真的很……特别。
有点怪,但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时髦感。
梁锦成立刻拍板,第一批,生产五百件。
五百件,对当时的锦绣服装厂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如果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损失惨重。
全厂上下,除了梁锦成和我,几乎没有人看好这款衣服。
连车间的女工们,都在私下里议论。
“那个林设计师,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设计出这么个怪物。”
“就是,跟唱大戏的戏服似的。”
我听到了,心里很难受,但我什么也没说。
我只能在心里暗暗祈祷,我的设计,一定要被市场接受。
第一批货出来后,梁锦成没有急着铺货到深圳的商场。
他动用了他在香港的关系,把这批货,送到了香港旺角的一些潮流服装店里寄卖。
他说:“要让潮流,从香港吹过来。”
等待消息的那几天,是我人生中最煎熬的日子。
我吃不下,睡不着,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钟叔见我这样,大概也于心不忍,偶尔会安慰我一句。
“小林啊,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做生意嘛,总有输有赢。”
我苦笑着点点头。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生意。
这是我的第一份作品,是我的尊严,也是梁锦成对我的信任。
我不能输。
一个星期后,梁锦成把我叫到办公室。
他的表情很平静,看不出喜怒。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香港那边,来电话了。”他说。
“怎么样?”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他没有直接,而是拉开抽屉,拿出了一份传真。
“你自己看。”
我颤抖着手接过那张薄薄的纸。
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繁体字和数字。
我一眼就看到了最下面的那个总数。
“售罄。”
两个字。
我愣住了。
“售罄是什么意思?”我傻傻地问。
梁锦成终于忍不住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售罄的意思就是,五百件,一件不剩,全卖光了!而且,他们还追加了三千件的订单!”
轰的一声。
我感觉自己的脑子炸开了。
幸福,像潮水一样,瞬间将我淹没。
我捂着嘴,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成功了。
我真的成功了!
那一天,梁锦成在工厂的食堂,加了餐。
红烧肉,白切鸡,还有我最爱吃的辣椒炒肉。
他举起酒杯,对着全厂的工人说:“今天,我们要庆祝!也要感谢我们的首席设计师,林蔓小姐!”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那些曾经怀疑的、不屑的目光,此刻都变成了惊讶和佩服。
钟叔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老脸通红。
“小林……不,林设计师。之前是老头子我有眼不识泰山,我给你赔个不是。”
他把一杯白酒,一饮而尽。
我的眼眶又湿了。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和压力,都烟消云散。
蝙蝠衫火了。
火得一塌糊涂。
先是在香港,然后风潮很快就吹回了深圳,吹向了全国。
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穿着各种颜色蝙蝠衫的年轻女孩。
锦绣服装厂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工厂从一个几百人的小厂,迅速扩张到上千人。
机器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转,工人们三班倒,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光芒。
因为,梁锦成给全厂工人都发了双倍的工资和奖金。
而我,拿到了我人生的第一笔提成。
三千件订单,总销售额三十万,百分之一的提成,是三千块。
当梁锦成把一个装着三千块现金的厚厚的信封交给我时,我的手都在抖。
三千块!
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滚烫的梦想。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宿舍。
我一个人去了深圳最贵的西餐厅,点了一份我只在杂志上见过的牛排。
我学着邻桌的人,笨拙地用着刀叉,喝着酸涩的红酒。
我看着窗外,深圳的夜景,灯火辉煌,像一条流淌的星河。
我知道,从今天起,我的人生,不一样了。
我不再是那个在东门摆地呈、为三块五块钱发愁的林蔓了。
我是设计师,林蔓。
成功来得太快,有时候会让人飘飘然。
但我没有。
因为梁锦成很快就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一款爆品,只能让你吃饱。想要做成一个品牌,你需要有持续不断的好设计。”
他说,“市场是残酷的,消费者的口味变得比翻书还快。今天他们追捧你,明天就可能忘了你。”
我冷静下来,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我开始更加疯狂地工作。
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其余的时间,不是在画图,就是在逛市场,或者泡在图书馆。
深圳当时有个地方叫“电子大厦”,那里能买到很多香港走私过来的“禁书”和杂志。
我成了那里的常客。
我开始尝试更多的风格。
石磨牛仔裤、高腰哈伦裤、荷叶边衬衫、丝绒连衣裙……
我的设计,不再局限于某一种风格,而是变得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大胆。
锦绣服装厂,也因为我这些层出不穷的新款,生意蒸蒸日上。
我们甚至开始有了自己的品牌——“蔓”。
用我的名字命名的品牌。
这是梁锦成提出来的。
他说:“你是我们品牌的灵魂。”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
我有了自己的品牌,有了不菲的收入。
我把老家的父母弟妹都接到了深圳,给他们买了套房子。
我看着他们在新家里开心的样子,觉得之前吃的所有苦,都值了。
但,树大招风。
“蔓”牌的成功,也引来了无数的模仿者和觊觎者。
市面上开始出现大量的仿冒品。
那些仿冒品,用着最差的面料,最粗糙的做工,却贴着和我们相似的商标,用极低的价格冲击着市场。
梁锦成气得在办公室里摔杯子。
“这帮人,简直就是吸血鬼!”
我们想过去告他们,但那个年代,知识产权的保护几乎是一片空白。
我们根本无从下手。
更可怕的是,我们发现,公司内部,好像出了内鬼。
我们新款的设计图,刚画出来没几天,市面上就已经出现了仿版。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这意味着,有人把我们的核心机密,泄露了出去。
梁锦成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几个核心部门的主管,包括钟叔。
因为能接触到设计图和版样的,只有他们几个人。
工厂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大家互相猜忌,人心惶惶。
我心里也很难受。
我不相信钟叔会背叛我们。
他虽然脾气不好,但为人正直,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
为了查出内鬼,我跟梁锦成商量了一个计划。
我故意放出消息,说我设计了一款全新的、颠覆性的秋冬大衣,将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产品。
然后,我画了三份完全不同的设计稿,分别命名为A、B、C。
A稿,我交给了生产部主管。
B稿,我交给了销售部主管。
C-稿,我锁在了自己的保险柜里,但故意把钥匙“不小心”掉在了钟叔的办公室。
我跟梁锦成说,真正的设计稿,一份都没有给出去。
这三份,都是假的。
我们要看的,是市面上最终会出现哪一款仿品。
那几天,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我害怕看到结果,又渴望看到结果。
如果内鬼真的是钟叔,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一个星期后,梁锦成的一个朋友,从另一家服装厂里,拿到了一件仿冒我们“新款大衣”的样衣。
当那件样衣摆在我们面前时,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是A稿。
那个版型,那个细节,和我画的A稿,一模一样。
内鬼,是生产部主管,老王。
老王是跟着梁锦成一起创业的元老,平时看起来忠厚老实,谁也没想到会是他。
梁锦成把他叫到办公室,把那件仿冒的样衣,扔在他面前。
老王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他什么都招了。
原来,是另一家服装厂,用双倍的工资和分红,把他给挖走了。
条件就是,让他把“蔓”牌的设计稿,偷偷带过去。
事情水落石出。
钟叔的嫌疑洗清了。
他气得冲进办公室,指着老王的鼻子骂。
“王八蛋!你对得起梁生吗?对得起厂里几千号兄弟姐妹吗?”
老王低着头,一言不发。
梁锦成没有骂他,只是很平静地对他说:“你走吧。看在多年情分上,我不报警。你好自为之。”
老王走了。
看着他落寞的背影,我心里五味杂陈。
深圳这个地方,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诱惑。
有的人,抓住了机遇,一飞冲天。
有的人,抵不住诱惑,跌入深渊。
这件事,给我和梁锦成都敲响了警钟。
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个企业,除了要有好的产品,还要有好的管理,和能留住人心的制度。
我们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给核心员工配股,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
工厂变得越来越规范,也越来越有凝聚力。
而我,也在这场风波中,迅速成长。
我不再是那个只知道埋头画图的小姑娘了。
我开始学习管理,学习市场,学习怎么去运营一个品牌。
梁锦成,成了我最好的老师。
他教我怎么看财务报表,怎么跟客户谈判,怎么判断市场的走向。
我们一起出差,一起去欧洲看时装秀,一起为了一个设计细节争得面红耳赤。
我们的关系,也早已超越了普通的老板和员工。
我们是战友,是知己。
有时候,我看着他专注工作的侧脸,心里会泛起一丝异样的情愫。
但我不敢多想。
他是有家室的人。
他的太太和孩子,都在香港。
我告诉自己,林蔓,你要清醒。
事业,才是你在这个城市安身立命的根本。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九十年代。
深圳,已经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都市。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马路上的车越来越多。
“蔓”牌,也成了国内小有名气的女装品牌。
我们在全国开了几十家专卖店,有了自己的办公大楼。
我也从那个住在农民房里的小丫头,变成了别人口中的“林总”。
我有了自己的车,自己的房子。
我甚至还把英语捡了起来,能跟外国客户进行简单的交流。
一切,都好得像一场梦。
但是,新的危机,也悄然而至。
随着国门的进一步开放,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品牌,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ZARA, H&M……
它们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快时尚。
款式更新快,价格便宜,对我们的本土品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我们的销售额,开始出现下滑。
仓库里的存货,越来越多。
公司的股东们,开始有怨言。
“林总,我们的设计是不是太老土了?跟不上年轻人的潮流了?”
“梁总,是不是应该请个国外的设计师来,给我们换换血?”
我和梁锦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吵架。
他觉得我应该向市场妥协,做一些更商业化、更“安全”的设计。
我觉得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风格,用更好的品质和设计,来留住客户。
“梁锦成,你忘了我们当初是怎么成功的吗?”我红着眼睛冲他吼,“就是因为我们够特别!现在你要我去做那些千篇一律的东西,不可能!”
“林蔓,你清醒一点!”他也拍了桌子,“现在不是讲情怀的时候!公司几千人要吃饭!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完蛋!”
那是我们认识以来,吵得最凶的一次。
我摔门而出,一个人开车去了海边。
我把车停在路边,看着远处的大海,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感觉很累,很孤独。
我好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车窗被人敲响了。
我回头,看到了梁锦成。
他手里拿着两罐啤酒。
他拉开车门,坐到副驾驶座上,把一罐啤酒递给我。
“还在生气?”
我没说话,拉开拉环,猛灌了一口。
冰冷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去,呛得我直咳嗽。
“对不起。”他忽然说,“今天是我太急了。”
我愣住了。
认识他这么多年,我从没听过他说“对不起”。
“我只是……只是太怕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怕失去我们一起打拼下来的这一切。”
我看着他,路灯的光,照在他疲惫的脸上,眼角的皱纹,比以前深了很多。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我也有错。”我说,“我不该那么固执。”
我们在车里,沉默了很久。
海风吹进来,带着咸湿的味道。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梁锦成说,“我们必须改变。”
“怎么改?”
“走出去。”他说,“去米兰,去巴黎,去时尚的中心看一看。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学学别人的东西。”
“然后,再回来,做我们自己的东西。”
他的话,像一盏灯,照亮了我心中的迷雾。
是啊。
闭门造车,是死路一条。
我们决定,放下国内的一切事务,一起去欧洲游学半年。
这个决定,遭到了公司所有股东的反对。
他们觉得我们是疯了,在公司最危急的时候,两个主心骨居然要跑出去玩。
但我们很坚决。
我们把工作交接好,然后登上了去巴黎的飞机。
那半年,是我们人生中最轻松,也最充实的一段时光。
我们像两个普通学生一样,去听课,去逛美术馆,去看各种各样的秀。
我们在塞纳河边散步,在佛罗伦萨的小巷里吃冰淇淋,在米兰大教堂前喂鸽子。
我们聊设计,聊艺术,聊人生,聊未来。
我发现,抛开工作的压力,他其实是一个很风趣、很有魅力的男人。
我心里那份被压抑了很久的情感,开始不受控制地疯长。
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我们在一家小酒馆里,喝了很多酒。
借着酒劲,我问他:“你……爱你太太吗?”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摇了摇头。
“那是家族的联姻,没有感情。”
我的心,狂跳起来。
“那你,为什么不离婚?”
“为了孩子。”他说,“也为了公司的稳定。我的很多生意,都和我太太的家族有关。”
我明白了。
他是被困在笼子里的鸟,即使翅有飞翔的力量,也挣不脱现实的枷锁。
那天晚上,我们回酒店的时候,他忽然拉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心很烫。
“阿蔓,”他看着我的眼睛,叫了我的小名,“如果……如果我能早点遇见你,就好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踮起脚,吻上了他的唇。
那个吻,带着酒精的味道,也带着多年的压抑和渴望。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错误。
但那一刻,我们谁也不想清醒。
从欧洲回来后,我们都很有默契地,没有再提起那个晚上的事。
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我们对“蔓”牌,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革新。
我们引进了新的面料,新的工艺,我们请了最好的摄影师和模特,拍了全新的广告大片。
我们的设计,也变得更加成熟和国际化。
既保留了东方的韵味,又融入了西方的剪裁。
新的“蔓”,像一只涅槃的凤凰,惊艳了整个市场。
我们的销售额,开始止跌回升,甚至超过了以前的巅峰。
我们成功地度过了危机。
事业上的成功,却无法填补我内心的空虚。
我和梁锦成的关系,变得很微妙。
在公司,我们是默契的搭档。
私底下,我们却刻意保持着距离。
我们都害怕,那层窗户纸一旦被捅破,会毁掉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
直到有一天,他的太太,从香港来了。
她直接冲进了我的办公室。
那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女人,穿着香奈儿的套装,戴着鸽子蛋大的钻戒。
她把一沓照片,狠狠地摔在我的办公桌上。
照片上,是我和梁锦成在巴黎街头拥吻的画面。
“!”她指着我的鼻子骂,“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勾引我老公!”
我浑身冰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办公室外面,围满了看热闹的员工。
我感觉自己像被扒光了衣服,扔在人群中。
所有的尊严,都碎了一地。
梁锦成很快就赶来了。
他把他太太拉了出去。
办公室的门关上了,但我依然能听到外面激烈的争吵声。
那天之后,梁锦成就再也没有来过公司。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他律师寄来的信。
信上说,他把他名下所有“蔓”牌的股份,都转让给了我。
从此以后,“蔓”牌,由我一个人全权负责。
信的最后,是他亲手写的一句话。
“阿蔓,对不起。忘了我,好好走下去。”
我拿着那封信,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哭得撕心裂肺。
我失去了他。
也失去了我曾经以为的爱情。
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从那段痛苦中走出来。
我把所有的悲伤,都化作了工作的动力。
我带着“蔓”牌,走得更高,更远。
我们开了更多的分店,我们甚至把店开到了香港,开到了巴黎。
我成了别人口中成功的女企业家,时尚界的女魔头。
我身边,也出现过很多追求者。
有年轻帅气的男模特,有成熟稳重的商界精英。
但我都拒绝了。
因为我的心里,再也装不下任何人了。
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他。
想起87年那个闷热的下午,他穿着白衬衫,出现在我的地摊前。
想起他带我走进那个充满希望的工厂。
想起我们一起熬过的无数个夜晚,一起分享过的喜悦和泪水。
他是我人生的伯乐,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爱过的人。
他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给了我一片天空。
然后,又决绝地转身离开。
有一年,我去香港出差。
鬼使神差地,我走进了中环的一家咖啡馆。
然后,我看到了他。
他就坐在窗边的位置,正在看报纸。
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背也有些驼了。
但他戴着金丝眼镜,斯文儒雅的样子,一点也没变。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看了很久很久。
我没有走过去。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
服务生问我:“小姐,请问几位?”
我回过神,对他笑了笑。
“一位。”
我选了一个离他很远的角落坐下。
点了一杯咖啡。
咖啡很苦,像我的人生。
但也有一丝回甘,像那些无法磨灭的,温暖的记忆。
我喝完咖啡,就离开了。
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发现我。
这样,也挺好。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回到深圳,我站在自己公司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我奋斗了半生的城市。
灯火璀璨,车水马龙。
这里,有我的青春,我的梦想,我的血泪,我的一切。
我拿起手机,拨通了助理的电话。
“通知设计部,明天上午九点开会。我们下一季的主题,叫‘回归’。”
回归初心。
回归到那个,在东门地摊上,用一针一线,缝制梦想的,二十岁的林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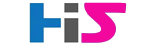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