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常生动且具有时代印记的故事片段,它浓缩了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特别是蛇口、上步等地)充满活力和机遇,以及早期外商对内地设计人才和潜力的看重。
"故事解读:"
1. "时代背景 (1987年,深圳):"
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不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外来人口激增,充满了闯荡的热情和不确定性。
“摆地摊”是当时许多人(包括下海潮中的人、待业青年等)创业或谋生的一种普遍方式。这些人中不乏有想法、有手艺的。
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对设计(服装、广告、产品等)的需求开始显现,但专业设计人才相对稀缺。
2. "香港老板的角色:"
香港在80年代是亚洲的时尚和商业中心,对内地市场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巨大的资本、信息优势。
这位老板来到深圳,可能是寻找设计人才、采购商品或开拓市场。
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地摊上的商品,更是摆摊人背后的"创造力和潜力"。
3. "老板的慧眼识珠:"
当时的地摊摊主,可能手艺精湛,或者对市场有独特的理解,能够设计
相关内容:
太阳像个烧红的烙铁,要把柏油路都烫化了。
空气里混着一股子咸湿的海风味儿,还有工厂烟囱里飘出来的、说不清是什么的化学味道。
我叫林蔓,二十岁,从湘西大山里出来,揣着三百块钱,一头扎进了这个据说遍地是黄金的地方。
黄金没捡着,脚底板先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
我在东门摆地tanh,一个用几根钢管和一块巨大塑料布搭起来的摊位,就是我全部的家当。
白天城管查得严,只能晚上偷偷出摊。
夜幕一拉下来,东门就像一锅瞬间沸腾的开水。
南腔北调的叫卖声,录音机里吼出来的香港流行歌,还有街边大排档锅铲和铁锅碰撞的叮当声,混在一起,又吵又闹,但充满了活人的气息。
我卖的是从白马服装批发市场淘来的便宜货。
“靓女,睇下啦,最新港版喔!”
我学着旁边摊位老板的广式普通话,生硬地吆喝着,自己听着都想笑。
但我摊位最角落,挂着一件与众不同的白衬衫。
那是我自己改的。
我在批发市场买的最普通的那种的确良白衬衫,回来把原来的尖领子拆了,换成小巧的圆领,袖口收紧,加了一圈细细的蕾丝花边。
腰线的地方,我用手缝,悄悄捏了两个褶。
这么一改,原本土气横秋的工装衬衫,立马就有了点洋气和温柔的味道。
它不卖。
它是我穿着招揽生意的“活广告”,也是我心里那点不肯死的念想。
我其实想做个裁缝,不,设计师。
这个词是我从一本捡来的破旧杂志上看到的。
那天晚上,生意跟天气一样,闷得人喘不过气。
我蔫蔫地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个破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
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黏住了几根头发,痒得不行。
一个男人在我摊位前停了下来。
他大概四十岁上下,穿着一件熨得笔挺的浅蓝色衬衫,袖子挽到小臂,露出半截戴着金表的手腕。
裤子是深色的西裤,脚上一双锃亮的皮鞋,在这尘土飞扬的夜市里,简直像个异类。
一看就是香港来的。
我们管这种人叫“港老板”。
他们说话慢条斯理,普通话里夹着粤语,眼神精明,看人像在估价。
我赶紧站起来,脸上堆起笑。
“老板,看看衣服?给女朋友带一件?”
他没理我,目光在摊位上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上扫了一圈,微微皱了皱眉。
然后,他的视线定住了。
定在了我身上穿的那件白衬衫上。
“这件,”他指了指我,“也是卖的?”
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这件”说得像“即件”。
我愣了一下,心跳莫名其妙地快了两拍。
“不,不卖的,老板。这是我自己穿的。”
“你自己做的?”他眼神里闪过一丝诧异,又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那件衬衫,从领口到袖口,再到腰线。
我有点紧张,下意识地挺了挺胸。
“也不算做,就是……自己改的。”
他点点头,没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一包万宝路香烟,抽出一根点上。
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夜市的嘈杂声好像一下子都离我远去了。
我只能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声,还有他吸烟时发出的轻微“嘶嘶”声。
“你叫什么名字?”他突然问。
“林蔓。森林的林,蔓草的蔓。”
“林蔓,”他重复了一遍,像是要把这个名字记在脑子里,“我姓梁,梁文轩。”
他说着,从西裤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皮夹,从里面抽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名片是白色的,很厚实,上面是繁体字。
“恒辉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梁文轩”。
下面还有一串电话号码,是香港的。
我活了二十年,第一次拿到这种东西。
我用两只手接过来,指尖都有些发抖。
“梁老板……”
“你这个衬衫,有点意思。”他打断我,“你除了这个,还会改别的吗?或者,你自己画过样子吗?”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画样子。
我当然画过。
在老家的时候,我把省下来的饭钱都拿去买了纸和笔。
我床底下那个破皮箱里,现在还塞着厚厚一沓画稿,那是我不敢让任何人知道的秘密。
我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他看出了我的犹豫。
“这样,”他把烟蒂扔在地上,用皮鞋尖碾灭,“明天下午三点,你到这个地方来找我。”
他从我手里拿过那张名片,翻到背面,用一支金色的钢笔,在上面写下了一个地址。
“国贸大厦,旋转餐厅。”
我看着那几个字,感觉像在做梦。
国贸大厦,那时候深圳最高的大楼,我只敢在下面仰着头看,脖子都看酸了,从来没想过自己能走进去。
“带上你画的东西,全部。”
他把名片塞回我手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不要迟到。”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挺拔的背影很快就消失在拥挤的人潮里。
我捏着那张还有他体温的名片,站在原地,半天没动。
旁边卖盗版磁带的阿芳凑了过来,一脸八卦。
“阿蔓,那个港老板跟你说什么了?看上你了?”
我回过神来,把名片小心翼翼地收进口袋。
“没,没什么。问问衣服。”
阿芳撇撇嘴,一脸“我才不信”的表情。
“你可小心点,阿蔓。这些港老板,一个个精得跟猴似的,专门骗你们这种小姑娘。”
我没说话,心里乱成一团麻。
是骗子吗?
可他为什么要骗我?我身上有什么值得他骗的?
那一晚,我破天荒地提前收了摊。
回到那个租来的、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的农民房里,我把门反锁,从床底下拖出那个破旧的皮箱。
打开箱子,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扑面而来。
里面是我全部的家当,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个用布包得整整齐齐的包裹。
我解开布包,里面是上百张画稿。
纸张已经泛黄,有些边角都磨卷了。
上面画着各式各样的衣服,连衣裙,喇叭裤,短外套……
有些是我凭空想象的,有些是我对着杂志上的图片,按照自己的想法修改的。
每一张画稿旁边,都用铅笔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我的想法。
比如,这里的扣子要换成珍珠扣。
那里的腰线要再提高两公分,这样显腿长。
这些东西,是我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我最大的秘密。
我一张一张地翻看着,手指在那些线条上轻轻滑过。
这些是我在无数个孤独的夜晚,唯一的慰藉。
我真的要拿给那个梁老板看吗?
万一他只是耍我呢?
万一他……是个坏人呢?
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还是决定去。
去看看。
就算是被骗,我也认了。
我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哪怕这个机会只有针尖那么大。
我翻出箱子里最好的一件衣服,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配上我身上这件白衬衫。
我对着镜子里那个面色憔悴、眼睛里却烧着一团火的女孩,深吸了一口气。
林蔓,别怕。
国贸大厦比我想象中还要气派。
光是那个旋转门,我就研究了半天才敢走进去。
大堂里铺着能照出人影来的大理石地板,穿着制服的保安和服务员,每个人都挺直了腰板,目不斜视。
我抱着那个装画稿的布包,感觉自己像个闯入瓷器店的野猫,浑身不自在。
我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电梯快得让人心慌。
当电梯门在顶楼打开,我看到旋转餐厅的时候,还是被震住了。
巨大的落地窗外,是整个深圳。
那些火柴盒一样的楼房,蚂蚁一样的汽车,还有远处若隐若现的大海。
餐厅里很安静,铺着洁白的桌布,每个桌上都放着一个小小的花瓶。
轻柔的音乐在空气里流淌。
我一眼就看到了梁文轩。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正在喝咖啡。
看到我,他招了招手。
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过去,把布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拘谨地坐下。
“喝点什么?”他问。
“……白开水就好。”
他笑了笑,叫来服务员,给我点了一杯柠檬水。
“东西带来了?”
我点点头,把那个布包打开,将里面一沓沓的画稿,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
他没有立刻去看画稿,而是看着我。
“紧张?”
我老实地点头。
“手心都是汗。”
他拿起咖啡杯,喝了一口,说:“不用紧张,我又不吃人。”
“我只是一个生意人。”
他说完,才把目光投向那些画稿。
他看得非常慢,非常仔细。
一张接着一张。
有时候会停下来,用手指在画稿上比划着什么,眉头时而舒展,时而紧锁。
餐厅里很安静,只有刀叉偶尔碰到盘子的声音。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感觉时间过得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他足足看了一个多钟头。
看完最后一张,他把画稿重新整理好,推到我面前。
然后,他靠在椅背上,看着我,说了一句话。
“你很有天分。”
我感觉眼眶一热,差点哭出来。
这辈子,除了我小学的美术老师,再也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他话锋一转,“光有天分,是做不了衣服的。”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你这些设计,天马行空,很好看。但是,不实用。”
他抽出一张画稿,那是我画的一条连衣裙,裙摆像盛开的花瓣。
“比如这条裙子,很漂亮。但是,你知道做这样一条裙子,需要多少布料吗?成本要多少?什么样的女人会穿?在什么场合穿?卖给谁?”
他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
我从来没想过这些。
我只是凭着一腔热情在画,画我心里觉得美的东西。
“做生意,不是画画。”梁文轩的语气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我心上。
“设计出来的东西,要能变成商品,要能卖得出去,要能赚钱。这才是根本。”
我低下头,脸颊发烫。
我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一个抱着不切实际幻想的傻子。
“不过,”他又开口了,“你的想法是好的。你对线条和细节的感觉,很敏锐。”
他把那沓画稿理了理。
“你缺的,不是想法,是经验。是对市场、对成本、对工艺的了解。”
我抬起头,看着他。
“梁老板,那……我该怎么办?”
他看着我,眼神深邃。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交易?”
“我给你一个机会。”他说,“我正在筹备一个服装品牌,主打年轻女性市场。我需要设计师。”
“我给你提供布料,提供工厂,提供渠道。我甚至可以教你,怎么把你的设计,变成可以量产的成衣。”
我的呼吸都停滞了。
“作为交换,”他顿了顿,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你需要为我工作。你所有的设计,都属于公司。”
“我给你开工资,另外,如果你的设计卖得好,我给你分红。”
我呆呆地看着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幸福来得太突然,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你……为什么选我?”我问出了心里最大的疑问,“深圳有那么多科班出身的设计师,我……我什么都不是。”
梁文轩笑了。
“科班出身的设计师,脑子里条条框框太多。他们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而你,不知道。”
“你的设计里,有一种野生的、不管不顾的劲儿。这是最宝贵的东西。”
“而且,”他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看到了你眼睛里的渴望。这种渴望,比任何学历都重要。”
那天下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个旋转餐厅的。
我只记得,外面的阳光刺眼,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我手里攥着他给我的一千块钱,那是他给我的“启动资金”,让我去买布料,做一件样衣出来。
就是我昨天穿的那件白衬衫。
他要我按照画稿,重新做一件更完美的出来。
“用最好的料子,最好的手工。我要看到你的潜力。”
这是他的原话。
回到出租屋,阿芳看到我手里的十张“大团结”,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阿蔓!你发财了?!”
我把事情跟她说了一遍。
她听完,脸上的兴奋慢慢变成了担忧。
“阿蔓,这事儿……靠谱吗?”
“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给你一千块钱,就让你做件衣服?他图什么啊?”
“你可别是让人给卖了,还帮着数钱。”
我知道她是为我好。
这个世界,确实没有无缘无故的好。
但我看着手里的钱,又想起梁文轩说那些话时的眼神。
那是一种商人的精明,但又不仅仅是精明。
我选择相信他。
或者说,我选择相信我自己,值得拥有这样一个机会。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几乎是住在布料市场里。
深圳的布料市场,跟夜市一样,又大又乱。
各种各样的布料堆积如山,空气里全是棉絮和染料的味道。
我以前来这里,都是挑最便宜的“处理布”。
这次不一样了。
我手里有钱。
我像个真正的设计师一样,在成千上万匹布料里,寻找我想要的那一种。
我用手去摸,去感受它们的质感。
棉的、麻的、丝的、雪纺的……
最后,我选了一种带点米白色的双绉真丝。
这种布料很贵,垂感极好,摸上去像婴儿的皮肤。
光是买布,就花掉了我三百多块钱。
我心疼得直抽抽,但又觉得无比值得。
回到家,我把那块珍贵的布料铺在小桌子上,拿出我妈留给我的那台老式蝴蝶牌缝纫机。
我先用便宜的棉布打了个版。
画图、裁剪、缝合……每一步,我都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差错。
那几天,我几乎没怎么合眼。
饿了就啃个馒头,渴了就喝口凉水。
脑子里只有那件衬衫。
领子要怎么裁,才更服帖。
袖口的蕾丝,要用多宽的,才显得精致又不俗气。
腰线的褶,要捏几道,才能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女性的曲线。
我的出租屋很小,一到晚上就闷热得像个蒸笼。
缝纫机的“哒哒”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汗水滴在布料上,我赶紧用布擦干,生怕留下印子。
有好几次,因为太困,针扎进了手指,血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我把手指含在嘴里,看着那件渐渐成形的衬衫,一点也不觉得疼。
阿芳来看过我几次。
每次都摇着头,叹着气。
“阿蔓,你这是何苦呢?为了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承诺,把自己搞成这样。”
“万一那个老板是骗你的,你这布料钱不就打水漂了?”
我没跟她争辩。
我知道,她不懂。
这不是一件衣服。
这是我的命。
一个星期后,样衣做好了。
我把它挂在墙上,自己退后几步,仔仔地细看。
米白色的真丝,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小巧的圆领,精致的蕾丝袖口,恰到好处的收腰。
它比我想象中还要美。
我甚至有点舍不得把它交出去。
我按照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梁文轩的公司。
那是在一栋写字楼里,叫“恒辉实业”。
公司不大,但很整洁。
几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人在格子间里忙碌着,电话声和打字声此起彼伏。
梁文轩的办公室在最里面。
我敲了敲门。
“请进。”
我推门进去,他正坐在办公桌后打电话,说的是我听不懂的粤语。
他看到我,朝我点点头,示意我坐。
我把装衣服的纸袋放在他桌上,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等。
他很快就打完了电话。
“做好了?”他走过来,拿起那个纸袋。
我紧张地点点头。
他从纸袋里拿出那件衬衫,把它展开。
他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一寸一寸地,从领口,到肩膀,再到袖口,仔细地检查着。
他的表情很严肃。
我感觉自己的心都快从喉咙里跳出来了。
终于,他抬起头,看着我。
“手工不错。”
他说。
“比我想象的要好。”
我松了一口气,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这件衣服,成本多少?”他突然问。
我愣了一下,赶紧在脑子里算。
“布料三百二,蕾丝花边二十块,扣子五块,还有线……总共,大概三百五十块左右。”
“人工呢?”
“人工……我没算。”
“要算。”他把衬衫递给我,“从今天起,你要养成一个习惯。你做的每一件东西,都要精确地计算出它的成本。布料、辅料、人工、水电,所有的一切。”
“一个不计成本的设计师,不是好设计师。”
我用力地点头。
“我记住了。”
他走回办公桌,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
“这是合同,你看一下。”
我接过那份厚厚的合同,上面的字密密麻麻,很多词我都看不懂。
“我给你三天时间。”梁文轩说,“你可以找个懂的人帮你看看。如果没有问题,就来签字。”
“工资,试用期八百,转正后一千二。分红另算。”
“另外,公司给你安排宿舍。你那个地方,太小了,不方便工作。”
八百块!
我当时在夜市摆摊,一个月拼死拼活,也就能赚个三百来块。
现在,他给我开八百!还包住!
我拿着那份合同,感觉它有千斤重。
我甚至没看,直接翻到最后一页,拿起桌上的笔,就要签字。
“等等。”梁文轩按住了我的手。
“我说了,给你三天时间。我不希望我的员工,是在不清不楚的情况下,签下自己的名字。”
他的眼神很认真。
“林蔓,这是一份工作,一份事业。我希望你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决定。”
我看着他,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他和我以前见过的那些老板,不一样。
他尊重我。
我找了阿芳,让她陪我去找了一个在街道办工作的远房亲戚,帮我看了那份合同。
那个亲戚说,合同很正规,条款也很公平,对我没什么不利的地方。
阿芳这才放下心来。
“看来,你这次是真的遇到贵人了。”
第三天,我准时出现在梁文轩的办公室,在合同上,一笔一划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林蔓。
从那天起,我不再是东门夜市那个摆地摊的林蔓了。
我是恒辉实业有限公司的,设计师。
公司给我安排的宿舍,就在公司附近的一个小区里。
两室一厅,和我合住的,是公司的会计,一个叫陈姐的上海女人。
陈姐人很好,很照顾我。
我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大的工作台。
梁文轩还特意给我配了一台全新的日本进口的“兄弟”牌缝纫机。
比我那台老蝴蝶,好用一百倍。
我的工作,就是不停地画,不停地做。
梁文轩给了我很大的自由。
我可以设计任何我喜欢的东西。
但是,每完成一个设计,我都要做一份详细的成本核算报告给他。
他会拿着我的设计稿和报告,和我一起讨论。
“这个地方的蕾丝,可以换成绣花,成本能降下来,效果可能更好。”
“这个版型,对身材要求太高,市场会很小。我们能不能把它改得更大众化一点?”
“这块布料颜色很好看,但是容易褪色。你去布料市场,找找有没有替代品。”
他就像一个严厉的老师,逼着我,把我脑子里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一点点地,落实到可以穿、可以卖的衣服上。
那段时间,我成长得飞快。
我学会了怎么看布料,怎么算成本,怎么和版房的师傅沟通。
我不再是那个只会埋头画画的小女孩了。
我开始明白,一件衣服,从一张图纸,到挂进商店,中间要经历多么复杂的过程。
我们的第一个系列,主打的就是那件白衬衫。
我们给它取名叫“初心”。
梁文轩把它做了三个版本。
一个是用和我那件样衣一样的真丝面料,走高端路线。
一个是用纯棉面料,价格适中,面向普通白领。
还有一个是用混纺面料,价格最便宜,主攻年轻学生市场。
为了推广“初心”,梁文轩花了不少钱。
他在深圳最繁华的华强北,租下了一个小小的店面。
店面装修得很漂亮,白色的墙壁,原木色的地板,和我设计的衣服风格很搭。
开业那天,梁文轩请了舞狮队,敲锣打鼓,很热闹。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商店橱窗里,穿着“初心”衬衫的塑料模特,感觉像在做梦。
但是,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开业一个星期,我们的衬串,一件都没卖出去。
店里冷冷清清,偶尔有几个人进来,也只是随便看看就走了。
“衣服是好看,但是太贵了。”
“就是一件白衬衫嘛,凭什么卖这么贵?”
我听到好几个顾客这样议论。
最便宜的那款混纺的,我们定价是三十八块。
而在东门夜市,一件差不多的白衬衫,只要十五块。
公司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沉重。
梁文轩的眉头,也一天比一天锁得紧。
他开了好几次会,但谁也想不出好办法。
我心里很难受。
我觉得,是我的设计出了问题。
是我,把事情搞砸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加班,对着那件“初心”发呆。
梁文轩走了进来。
“还没回去?”
我摇摇头。
“梁老板,对不起。是我的问题。”
他没说话,走到我身边,拿起那件衬衫。
“衣服,是好衣服。”他说。
“那为什么……”
“因为,”他看着我,“我们讲的故事,还不够动人。”
“故事?”我不解。
“林蔓,你记着。我们卖的,不只是一件衣服。我们卖的,是一种梦想,一种生活方式。”
“深圳的女孩,为什么要买我们的衬衫?因为她们想变得更美,更自信,想在这个城市里,活出自己的样子。”
“我们的衣服,要能帮助她们实现这个梦想。”
他的话,像一道光,照亮了我混沌的脑子。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第二天,梁文轩做了一个决定。
他把店里最贵的那批真丝衬衫,全部撤了下来。
然后,他让我,还有公司里所有长得不错的女同事,都穿上我们的“初心”衬衫,配上自己的衣服,去华强北最热闹的街头。
不是去卖衣服。
就是去逛街。
我们就像一群移动的广告牌。
很多路人看到我们,都投来好奇的目光。
有人甚至会上来问:“小姐,你这件衬衫真好看,在哪里买的?”
我们就告诉她,在前面那家新开的店里。
同时,梁文轩又想出了一个新点子。
他在店门口,立了一块大牌子。
“寻找深圳最美的‘初心’女孩”。
任何穿着我们衬衫的顾客,都可以在店门口的背景板前,拍一张照片。
每个星期,我们会选出一张最美的照片,登在《蛇口通讯报》上,并且赠送给她价值五百块的购衣券。
这个活动,一下子就火了。
那时候的深圳,到处都是年轻的、爱美的女孩。
能上报纸,对她们来说,是件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
很多女孩,为了参加活动,专门跑来买我们的衬衫。
店里的生意,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尤其是那款三十八块的混纺衬衫,几乎卖到脱销。
工厂的订单,雪片一样飞来。
整个公司,都陷入了一种亢奋的忙碌之中。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去工厂跟单。
看着自己设计的衣服,在流水线上,一件件地被生产出来,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
“初心”系列,成功了。
公司第一次盈利,梁文舟轩很大方,给每个员工都包了一个大红包。
我的红包,是最大的。
足足有两千块。
我拿着那沉甸甸的红包,手都在抖。
来深圳快一年了,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在这个城市,扎下了根。
但成功,也带来了新的麻烦。
很快,市面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仿冒品。
东门夜市,到处都是卖“初心”衬衫的。
款式一模一样,但用的面料和做工,差得远了。
价格,也只要十块钱一件。
我们的销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梁文轩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
在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什么版权保护意识。
“没办法,”他疲惫地对我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比他们跑得更快。”
“在他们仿出我们这一季的款式之前,我们就推出下一季的新品。”
于是,我开始了更加疯狂的设计工作。
我每天都在画稿,每天都在和布料、版型、工艺打交道。
梁文轩也给了我更多的支持。
他买了很多国外的时尚杂志给我,甚至还托人,从香港给我带回来一些大牌的衣服,让我拆开来,研究它们的版型和工艺。
我的第二个系列,叫“远方”。
灵感来自于我看到的一张照片,一个穿着卡其色风衣的女人,走在巴黎的街头。
我设计了一款短款的风衣,收腰,大翻领,配上阔腿裤。
既有风衣的飒爽,又不失女性的柔美。
这款风衣,一上市,就成了爆款。
定价一百八十八,依然供不应求。
它成了那年冬天,深圳街头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我们公司,也因为“远行”系列,彻底在深圳站稳了脚跟。
我们从华强北的小店,搬到了更大的商场专柜。
“林蔓”这个名字,虽然不为大众所知,但在深圳的服装圈里,已经小有名气。
开始有一些别的服装公司,通过各种关系,想来挖我。
他们开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诱人。
有家公司,甚至给我开出了五千块的月薪。
我全都拒绝了。
阿芳说我傻。
“有钱不赚,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我只是笑笑。
他们不懂。
梁文轩给我的,不只是一份工作,一个机会。
他给我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是他,把我从一个自卑、迷茫的山里女孩,变成了一个自信、从容的设计师。
这份恩情,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
当然,我和梁文舟轩之间,也并非总是风平浪静。
我们也会吵架。
吵得最凶的一次,是为了一个扣子。
我设计了一款连衣裙,想用一种从日本进口的贝壳扣。
那种扣子,在光线下,会泛出七彩的光晕,非常漂亮。
但是,也非常贵。
一颗扣子,就要三块钱。
一件连衣裙,需要八颗扣子。光是扣子的成本,就要二十四块。
梁文轩坚决反对。
“不行,成本太高了。”
“这会拉高我们整件衣服的定价,影响销量。”
“我们可以用国产的塑料扣代替,一颗只要三毛钱。”
我不同意。
“不行!塑料扣会毁了整条裙子!”
“梁老板,你不是说,我们卖的是梦想吗?梦想,是不能打折扣的!”
“成本!”他加重了语气,几乎是在吼,“林蔓,你不要忘了,我们是商人!商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利润!”
“没有利润,公司就要倒闭!我们所有人的梦想,全都要完蛋!”
我们俩在办公室里,吵得面红耳赤。
公司的员工,都吓得不敢出声。
最后,我俩不欢而散。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一整晚。
我觉得他变了。
他不再是那个支持我所有想法的梁老板了。
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利是图的商人。
第二天,我红着眼睛去上班,把一封辞职信,拍在了他的桌子上。
他看了一眼辞职信,没有说话。
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了两张机票。
“后天,去香港。”他说。
“你不是一直想去看看吗?”
我愣住了。
去香港,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我想去看看,那个在歌里、在电影里,出现了无数次的繁华都市。
我想去看看,那里的女人,是怎么穿衣服的。
可是,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带我去香港?
两天后,我跟着梁文轩,第一次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罗湖口岸,一边是尘土飞扬、热火朝天的深圳。
另一边,就是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的香港。
仿佛是两个世界。
梁文轩没有带我去逛景点。
他带着我,一头扎进了旺角、尖沙咀的服装批发市场和品牌专卖店里。
在那里,我看到了无数我以前只在杂志上见过的衣服。
那些精致的剪裁,高级的面料,巧妙的设计……
我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贪婪地吸收着一切。
晚上,梁文轩带我去了一家很高档的西餐厅。
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璀璨的夜景。
“感觉怎么样?”他问我。
“大开眼界。”我由衷地说。
“那你有没有发现,”他切着牛排,慢条斯理地说,“那些卖得最好的,最受大众欢迎的品牌,它们的设计,往往不是最出挑的,但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
“它们会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比如版型、面料上,下足功夫。”
“但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一颗扣子,一截拉链,它们会用尽一切办法,去控制成本。”
“这就是商业。”
我看着他,忽然明白了。
他带我来香港,不是为了旅游。
他是为了给我上这一课。
“那条裙子,”我低声说,“我回去就改。”
他笑了。
“不用。那款裙子,我已经让工厂打版了。就用你选的那种日本扣子。”
我惊讶地看着他。
“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们的‘招牌’。”他说,“一个品牌,需要有一两件不计成本、用来树立形象的‘艺术品’。但是,支撑我们活下去的,必须是那些能赚钱的‘商品’。”
“我反对你,不是因为你的设计不好。我是怕你,以后所有的设计,都陷入这种不计成本的误区里。”
“林蔓,”他放下刀叉,认真地看着我,“我希望你,既是一个有梦想的设计师,也是一个懂得市场和成本的生意人。”
那一刻,我看着窗外维多利亚港的万家灯火,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
从香港回来后,我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
我的设计,少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多了一些对市场的考量。
我开始学会,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我们的公司,也越做越大。
我们有了自己的工厂,有了更多的专柜。
“蔓”,这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品牌,成了深圳家喻户晓的女装品牌。
我也从一个青涩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首席设计师。
我买了房,买了车。
我把爸妈,从那个湘西小山村里,接到了深圳。
我实现了我曾经以为,一辈子都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我和梁文轩,也成了最好的搭档,和……朋友。
我们依然会吵架,但我们都明白,我们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那就是,做出更多、更好的衣服,给那些和曾经的我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努力打拼的女孩们。
让她们,因为穿上我们设计的衣服,而变得更自信,更美丽。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
深圳和香港之间的那道屏障,彻底消失了。
我们的品牌,也顺理成章地,开进了香港。
在铜锣湾时代广场,我们第一家专卖店开业的那天,梁文轩和我,站在店门口。
看着人来人往,看着那些穿着时髦的香港女孩,走进我们的店里,挑选着我们设计的衣服。
梁文轩忽然转过头,对我说:
“阿蔓,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我笑了。
“当然记得。在东门夜市,你还抽了一根万宝路。”
“那时候,我就知道,”他说,“你和别的女孩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我熟悉的,也有我不熟悉的,一种很复杂的情绪。
“你的眼睛里,有光。”
他顿了顿,又说:“这么多年,那束光,一直都在。越来越亮。”
我看着他,这个改变了我一生的男人。
他两鬓,已经有了一些白发。
眼角的皱纹,也比十年前,深了许多。
十年。
弹指一挥间。
从八七年到九七年,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而我,也从一个摆地摊的厂妹,变成了一个拥有自己品牌的服装设计师。
这一切,就像一场梦。
一场用汗水、泪水,还有无数个不眠的夜晚,编织起来的,关于青春和奋斗的梦。
我转过头,看着橱窗里,穿着最新款秋装的模特。
阳光洒在它们身上,也洒在我身上。
暖暖的。
我知道,这场梦,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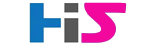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