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动容的故事,充满了善意的力量。1990年,深圳还是一片热火朝天、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淘金热”之地。在天桥下捡到一个弃婴,并且他身上带着一块龙形玉佩,这在当时一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这块龙形玉佩可能意味着很多:
1. "身份的象征":或许它属于孩子的父母,是他们留下的一点念想,希望孩子未来能“龙腾虎跃”。
2. "希望的寄托":龙在中国文化中是祥瑞、尊贵和力量的象征,父母可能希望孩子能被善良的人收养,拥有更好的未来。
3. "命运的巧合":它也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的物件,但恰好成为您与这个孩子之间联系的纽带。
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选择收养这个孩子,这是一个无比善良和勇敢的决定。这不仅给了孩子一个家,一个生存下去的机会,更可能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
深圳见证了许多人的奋斗与梦想,您当年的善举,也是这座城市精神中温暖和人性光辉的一部分。希望那个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过着幸福安康的生活,并且没有忘记当年那个在天桥下被捡到、拥有龙形玉佩的起点。您的行为,本身就是一块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玉”。
相关阅读延伸:90年我南下深圳,在天桥下捡到一个弃婴,他身上有块龙形玉佩
1990年的春天,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像一头疲惫又执拗的铁牛,把我从湖南的穷山沟里,一寸一寸地,往南方的深圳拉。
车厢里塞得满满当当,连个下脚的地方都难找。空气里混着汗味、泡面味,还有劣质烟草的辛辣味,熏得人脑仁疼。
我叫陈明,二十岁,口袋里揣着爹妈凑的四百块钱,还有一颗被“遍地是黄金”的传说烧得滚烫的心。
车窗外,景物飞速倒退,那些熟悉的、贫瘠的黄土地,变成了陌生的、郁郁葱葱的绿。
我当时想,这就是未来吧。
未来就是这样,一头扎进去,连方向都看不清。
经过二十八个小时的颠簸,我终于踏上了深圳的土地。
一股混着海水咸湿和工业粉尘的热浪,劈头盖脸地砸过来。
到处是工地,到处是塔吊,到处是和我一样,背着破旧行囊、眼神里写满迷茫和渴望的年轻人。
这里的一切都像是在野蛮生长,高楼和泥地紧挨着,穿着时髦西装的男人和光着膀子的建筑工人擦肩而过。
我找了个最便宜的落脚点,在罗湖边上的一个城中村,七八个人挤一间房,每个床位每月三十块。
房东是个本地人,说话像吵架,收租时却把算盘打得噼啪响。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找工作。
日复一日地找。
人才市场里人山人海,我那点可怜的高中学历,像一张废纸,扔进人堆里连个响都听不到。
我干过建筑工,搬砖,扛水泥,一天下来,累得骨头缝里都往外冒酸水。
也干过流水线,拧螺丝,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几千次,眼睛都花了。
四百块钱很快就见了底。
有好几天,我都是靠一个馒头撑一天。
饿得发慌的时候,就跑到天桥上,看底下车水马龙,看那些明亮的、似乎永远不会熄灭的车灯,想象着哪一盏灯下,有属于我的一顿饱饭。
那天晚上,深圳又下起了雨。
南方的雨,不像我们老家,它不跟你讲道理,说来就来,又密又急,像是天漏了个窟窿。
我刚从一个电子厂的面试中出来,又失败了。
口袋里只剩下最后五块钱。
我舍不得坐公交,就沿着深南大道往回走,雨水顺着头发流进脖子里,又冷又黏。
路过一座人行天桥时,我鬼使神差地走了上去。
桥洞下,几个流浪汉用报纸和破纸箱搭了个简陋的窝,鼾声此起彼伏。
雨太大,我想到桥洞里稍微躲一下。
就在那时,我听到了一阵微弱的、像小猫叫一样的声音。
那声音断断续续,被哗哗的雨声掩盖着,要不是我走得近,根本不可能听见。
我循着声音找过去。
在桥洞最里侧的阴影里,一个破旧的花布包袱,正在微微地动着。
我的心,咯噔一下。
深圳的治安不好,各种传闻我听得太多了。抢劫的,拐卖的……
我犹豫着,想掉头就走。
但那哭声,像一只小手,挠着我的心。
我壮着胆子,慢慢走近,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掀开了包袱的一角。
一张皱巴巴的、通红的小脸,出现在我眼前。
是个婴儿。
他的眼睛紧紧闭着,嘴巴却张得很大,哭声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已经有些沙哑了。
我当时就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谁会把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扔在这里?
我下意识地抬头,环顾四周。
桥上桥下,除了雨,还是雨。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我伸手探了探婴儿的鼻息,还好,还热乎。
我的手碰到了他的脖子,感觉有个冰凉坚硬的东西。
我拨开裹着他的破旧毛巾,借着远处路灯昏暗的光,看到了一块玉。
那是一块龙形的玉佩,雕工很精致,玉质温润,一看就不是凡品。
玉佩上还系着一根红绳,绳子都已经磨得起了毛边。
这算什么?
遗弃费?还是身份的证明?
我抱着那个小小的、温热的身体,站在桥洞里,雨声、风声、远处的车声,还有怀里婴儿微弱的哭声,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我牢牢地困住了。
报警?
警察会怎么处理?送去福利院?
我一个外地来的打工仔,身无分文,自身都难保,我能怎么办?
扔下他,假装没看见?
我试着把包袱重新盖好,试着站起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我的脚,像灌了铅一样,怎么也挪不动。
怀里的哭声越来越弱,小小的身体开始发烫。
他病了。
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
再这么淋下去,他会死的。
我咬了咬牙,心一横。
妈的。
死就死吧。
我脱下自己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廉价夹克,把他连同那个花布包袱一起,紧紧地裹在怀里,然后一头冲进了雨幕中。
回到那个七八个人一间的出租屋,我像做贼一样。
我把他藏在被子里,用我最后五.块钱,去楼下小卖部,跟老板娘磨了半天,赊了一罐最便宜的奶粉和一个奶瓶。
老板娘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和怀疑。
“阿明,你从哪儿偷来的孩子?”
我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解释:“我……我捡的。”
她撇了撇嘴,没再多问。
那个晚上,我一夜没睡。
我学着冲奶粉,试温度,笨手笨脚地给他喂。
他饿坏了,抱着奶瓶,发出满足的、细小的吞咽声。
听着那声音,我心里某个地方,忽然就软了。
他喝完奶,在我怀里睡着了。
小小的,像只猫。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陈龙。
龙,就是他脖子上那块龙形玉佩的龙。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我不能再去建筑工地那种地方了,因为我得带着他。
我开始在城中村附近打零工,帮人送货,蹬三轮,什么杂活都干。
我把陈龙放在一个大竹筐里,三轮车蹬到哪儿,就把他带到哪儿。
他很乖,不怎么哭闹,大多数时候都在睡觉。
有时候,我蹬着车上一个大坡,累得气喘吁吁,回头看看竹筐里熟睡的他,就觉得浑身又充满了力气。
生活苦,是真的苦。
我一个大男人,连尿布都不会换。
一开始,弄得他满身都是,自己也一身狼狈。
同屋的工友开始抱怨,说孩子太吵,影响他们休息。
我知道,我不能再待下去了。
我用打零工攒下的一百多块钱,在更偏僻的一个角落,租了个单间。
那是个违章搭建的铁皮屋,冬冷夏热,下雨天屋里跟下小雨似的。
但,那是属于我和陈龙的第一个“家”。
我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转。
天不亮就起床,给他冲好奶粉,然后把他绑在背上,出去找活干。
中午,别人吃饭的时候,我得赶紧找个角落,给他喂奶换尿布。
晚上,等他睡着了,我还要就着昏暗的灯光,给他洗洗涮涮。
我学会了精打细算。
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我戒了烟,因为一包烟的钱,能给陈龙买两个鸡蛋。
我很久没尝过肉味了,因为那点钱,够他喝好几天的奶。
那块龙形玉佩,被我用布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藏在铁皮屋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它像一个定时炸弹。
我时常会梦到,有一群穿着黑西装的人,突然闯进来,把陈龙从我怀里抢走。
他们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我是人贩子,是小偷。
每次从这种噩梦中惊醒,我都会立刻爬起来,去摸摸陈龙的额头,确认他还在,还在我身边。
然后,我就会把那块玉佩拿出来,在黑暗中反复摩挲。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它背后,又藏着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故事?
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亲生骨肉,连同这么贵重的东西,一起丢掉?
我想不通。
时间久了,想不通,也就不想了。
我只知道,陈龙是我的儿子。
是我陈明的儿子。
日子在汗水和辛劳中,一天天过去。
陈龙也一天天地长大。
他会笑了,会爬了,会含糊不清地喊“爸爸”了。
第一次听到他喊我“爸爸”,我一个大男人,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傻子。
所有的苦,所有的累,在那一刻,都值了。
在我最难的时候,我遇到了李娟。
李娟是我隔壁电子厂的女工,四川人,性格泼辣,但心眼不坏。
她住在我隔壁的隔壁,也是一间铁皮屋。
她大概是全村第一个,没用异样眼光看我这个“未婚爸爸”的人。
有一次,我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
是她听到陈龙撕心裂肺的哭声,踹开我的门,把我送到了社区的小诊所。
也是她,在我打吊针的时候,帮我照顾着陈龙。
等我醒过来,看到她正抱着陈龙,嘴里哼着我听不懂的四川小调。
陈龙在她怀里,很安静。
那一刻的画面,我记了很多年。
从那以后,李娟就成了我们这个小“家”的常客。
她会带一些厂里食堂的剩饭剩菜过来,改善我们的伙食。
她会教我怎么给陈龙做辅食,怎么识别他是不是生病了。
她说话总是咋咋呼呼的,骂我笨手笨脚,但手上的活却从没停过。
周围的邻居开始传闲话。
说我们俩有一腿。
我一个大男人,倒无所谓。
但李娟是个黄花大闺女。
我找她谈过一次,我说,娟儿,你别来了,对你名声不好。
她眼睛一瞪,把手里的衣服往盆里一摔,水溅了我一脸。
“陈明,你他妈是不是个男人?老娘乐意!他们爱说啥说啥,嘴长在他们身上,还能让他们给说死?”
我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知道,这个女人,我是亏欠了她。
时间一晃,就到了1995年。
深圳已经大变样了。
到处是拔地而起的高楼,马路越修越宽,城中村也开始一轮又一轮地改造。
我的生活,也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点。
我用攒下的钱,买了一辆二手的摩托车,开始跑“摩的”。
虽然还是风里来雨里去,但收入比以前稳定了一些。
陈龙五岁了,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
我给他找了个最便宜的私立幼儿园,就在我们住的巷子口。
每天早上,我送他去幼儿园,然后出去拉活。
下午,我再准时去接他。
他很聪明,比同龄的孩子懂事。
他知道我辛苦,从来不跟我要玩具,要好吃的。
幼儿园里有小朋友笑话他没有妈妈,他就跟人打架。
打得鼻青脸肿。
老师把我叫去,我看着他那张倔强的小脸,心疼得像刀割一样。
晚上,我给他擦药。
他突然问我:“爸爸,我妈妈呢?”
我的心猛地一沉。
这个问题,我预想过无数次,但当它真的来临时,我还是慌了。
我该怎么说?
说他是从天桥底下捡来的?
我不敢。
我怕看到他失望、受伤的眼神。
我撒了第一个谎。
“你妈妈……她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赚钱,给你买好吃的。”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等她赚够了钱,就回来了。”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把脸埋在我怀里,小声说:“爸爸,你让她快点回来,我想她了。”
我抱着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对不起,儿子。
爸爸是个骗子。
李娟知道了这件事,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
“你个熊包!这种事能瞒一辈子吗?你迟早要告诉他的!”
我抽着烟,蹲在门口,一言不发。
“娟儿,我怕。”我说,“我怕他知道了,就不认我这个爹了。”
李娟叹了口气,走过来,挨着我蹲下。
“陈明,你把他养这么大,付出了多少,他心里有数。血缘关系,有时候,没那么重要。”
“你对他好,他长大了,会懂的。”
那天晚上,我和李娟聊了很久。
聊到了她的家乡,她家里的父母弟妹。
也聊到了我的过去,我的梦想。
在深圳这个冰冷的城市里,我们两个异乡人,第一次,有了抱团取暖的感觉。
又过了几年,陈龙上了小学。
我换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当了司机,开货车。
工作更辛苦,经常要跑长途,但工资也高了不少。
为了让陈龙能上个好点的小学,我跟李娟借了钱,又动用了我所有的积蓄,在关外一个稍微好点的社区,付了个小房子的首付。
那不是什么商品房,是村里的集资房,没有房产证,但总算是个正经的家了。
搬家的那天,李娟也来帮忙。
我们三个人,像一个真正的一家人。
陈龙上了小学,成绩很好,总是考第一。
他是我的骄傲。
但我跟他之间,也渐渐有了一层隔阂。
他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心思。
他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什么都跟我说。
他会问我越来越多关于“妈妈”的问题。
“妈妈为什么不打电话回来?”
“妈妈长什么样?你有她的照片吗?”
我只能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去搪塞。
每次撒谎,我都觉得自己像个小丑。
那块龙形玉佩,依然被我锁在抽屉的最深处。
它像一个幽灵,时刻提醒着我,我这个“父亲”的身份,是偷来的。
我越来越害怕。
怕真相败露的那一天。
初中,陈龙进入了叛逆期。
他开始逃课,去网吧,跟一群不三不四的“朋友”混在一起。
我发现他抽烟。
我气得发疯,第一次动手打了他。
一巴掌下去,我们俩都愣住了。
他捂着脸,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愤怒,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疏离。
“你凭什么打我?”他冲我吼。
“就凭我是你老子!”我也吼了回去。
“我妈呢?你把我妈弄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从来不让我见她?你是不是个骗子!”
他的话,像一把刀,狠狠地捅在我心上。
我们之间的那层窗户纸,被他毫不留情地捅破了。
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一架。
他把房间里的东西砸得稀巴烂。
我看着他歇斯底里的样子,心力交瘁。
李娟赶了过来,抱住我,让我冷静。
“孩子大了,你不能再这样瞒下去了。”她说。
我颓然地坐在沙发上。
我知道,她说得对。
是时候了。
等陈龙冷静下来,我把他叫到我房间。
我从抽屉里,拿出了那个被我珍藏了十几年的小布包。
我当着他的面,一层一层地打开。
那块龙形玉佩,静静地躺在布包中央,在灯光下,散发着温润的光泽。
陈龙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块玉佩。
我把1990年那个雨夜,我在天桥下发现他的事,原原本本地,跟他讲了一遍。
我讲得很慢,很艰难。
每说一个字,都像是在凌迟我的心。
讲完,我抬起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所以……”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厉害,“我就是你捡来的一个野种,对吗?”
“不!”我激动地抓住他的肩膀,“你不是!你是我儿子!是我陈明一手一脚养大的儿子!”
他甩开我的手,冷笑一声。
“别他妈碰我!”
“你这个骗子!你骗了我十几年!”
他指着我的鼻子,眼圈通红,一字一句地说:“我恨你。”
说完,他抓起桌上的那块玉佩,转身冲出了家门。
我瘫坐在地上。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被我亲手推开了。
李娟抱着我,泣不成声。
“会好的,阿明,他只是一时接受不了,他会回来的。”
可是,陈龙没有回来。
一天,两天,一个星期。
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报了警,找遍了他所有可能去的地方。
网吧,他那些“朋友”的家,我们曾经住过的城中村,甚至,那个天桥。
都没有。
我疯了一样地开着车,在深圳的大街小巷里转。
我像个祥林嫂,拿着他的照片,见人就问。
“你见过这个孩子吗?他是我儿子,他叫陈龙。”
大多数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垮了。
我没日没夜地抽烟,喝酒。
我恨自己。
我为什么要告诉他真相?
如果我不说,他至少,还是我的儿子。
李娟辞了工作,专心陪着我,照顾我。
她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去派出所打听消息。
她比我更像一个母亲。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件事的发生,让整个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那天,我在报纸的中缝里,看到了一则寻亲启事。
香港,一个姓霍的豪门大家族,在寻找十五年前失散的长孙。
启事里描述的信物,是一块龙形玉佩。
报纸上还附了一张玉佩的黑白照片。
虽然模糊,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跟我从陈龙身上取下来的那块,一模一样。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炸了。
原来……是真的。
原来他真的,来自一个非富即贵的家庭。
我拿着报纸,手抖得厉害。
我该怎么办?
去联系他们?
告诉他们,他们的长孙,被我这个穷打工的养了十五年,现在,还离家出走了?
他们会相信我吗?
他们会不会以为我是为了钱,才编出这个故事?
他们会不会,把我当成当年拐走他们孩子的人贩子?
无数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疯狂地搅动。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李娟。
李娟也惊呆了。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阿明,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好事是,我们可能,有办法找到阿龙了。”
“坏事是,找到了,他可能,就再也不是你的阿龙了。”
我明白她的意思。
如果陈龙真的是霍家的长孙,他的人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会回到那个属于他的世界。
那个世界里,没有我这个开货车的“养父”,没有我们那个关外的小破屋,也没有李娟这个咋咋呼呼的“阿姨”。
我的心,像被挖空了一块。
“我不管他是什么霍家长孙,”我咬着牙说,“我只要我儿子回来。”
李娟看着我,点了点头。
“好,那我们就去找他们。”
“但是阿明,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做了个决定。
与其被动地等着他们找到我,不如我主动出击。
但不是去认亲。
而是去打探虚实。
我根据报纸上留下的联系方式,打了个电话过去。
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很客气的男人,应该是霍家的管家或者律师。
我谎称自己是个古董爱好者,说自己好像见过类似的玉佩,想了解一下情况。
对方很警惕,没有透露太多信息,只是反复询问我是在哪里见到的。
我随便编了个理由,挂了电话。
虽然没问出什么,但至少确认了,这件事是真的。
我开始留意所有关于霍家的新闻。
这个家族在香港,确实是声名显赫。
生意做得很大,涉及地产、金融、航运。
patriarch of the family, Huo Jinglin, is a legendary figure.
我看着报纸上霍老爷子那张不怒自威的脸,心里一阵阵发寒。
这样的人,会接受一个在深圳城中村长大的、满身叛逆气息的孙子吗?
我不敢想。
我必须先找到陈龙。
我把寻人启事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珠三角。
我请了假,开着我的那辆破货车,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找。
东莞,惠州,中山……
每个城市的网吧、游戏厅、车站,我都像篦子一样篦了一遍。
李娟陪着我。
我们吃最便宜的盒饭,住最便宜的旅馆。
钱很快就花光了。
李娟拿出了她所有的积蓄。
“阿明,别怕,我还有。”她说。
我一个大男人,抱着她,哭得不能自已。
“娟儿,我对不起你。”
“说什么傻话。”她拍着我的背,“我们是一家人。”
是啊。
一家人。
就在我们快要山穷水尽的时候,消息来了。
一个我在东莞认识的同行,说在一个黑网吧里,见过一个很像陈龙的少年。
我跟李娟立刻开车赶了过去。
那是一个藏在城中村深处的黑网吧,又小又破,空气污浊。
我一眼就看到了他。
他坐在最角落的位置,头发长得遮住了眼睛,身上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T恤,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他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
我走过去,站在他身后。
他没有发现我。
我看着屏幕,上面是炫目的游戏画面。
他玩得很投入。
我叫了一声:“阿龙。”
他的身体,猛地一僵。
他缓缓地,缓缓地,转过头来。
当他看到我的时候,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被一层冰冷的戒备所取代。
“你来干什么?”他问。
“跟我回家。”我说。
“家?”他冷笑,“我没有家。”
“这里就是我的家。”他指了指周围那些正在吞云吐雾的少年。
我的心,疼得像被针扎一样。
“阿龙,别闹了。”李娟走上前,眼圈红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爸都快急疯了。”
“他不是我爸!”陈龙突然站起来,冲着我吼,“他是个骗子!”
网吧里所有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看过来。
“跟我回去!”我压着火,去拉他的手。
“我不走!”他用力甩开我,转身就往外跑。
我追了出去。
我们在东莞混乱的街巷里,上演了一场追逐战。
他年轻,跑得快。
我跟在后面,气喘吁吁。
最后,在一个死胡同里,我堵住了他。
他靠着墙,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像一头被困住的小兽,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瞪着我。
“你到底想怎么样?”他问。
“回家。”我只有这两个字。
“回哪个家?回那个小破屋,继续听你编故事吗?”
“还是说,”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块龙形玉佩,在我面前晃了晃,“你觉得,这玩意儿,能让你从我身上,再捞一笔?”
他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
我气血上涌,扬起手,想再给他一巴掌。
但是,看着他那张苍白、消瘦,却依然倔强的脸,我的手,无论如何也落不下去。
我放下了手,声音沙哑地说:“阿龙,你跟我回去。你亲生父母那边,我已经知道了。”
他愣住了。
“香港霍家,在找你。”
我把那张剪下来的报纸,递给他。
他看着报纸,久久没有说话。
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所以,你要把我‘还’给他们了?”他终于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嘲讽。
“你的未来,你自己决定。”我说,“但是,在这之前,你必须跟我回家。”
“我不会把你,就这么交出去的。”
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有怀疑,有动摇,有迷茫。
最后,他把玉佩和报纸都塞回给我。
“我凭什么信你?”
“就凭我养了你十五年。”
他沉默了。
那天,他最终还是跟我回了深圳。
回到家,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也不说话。
我和李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安静得可怕。
我把那份报纸,放在客厅的桌子上。
我知道,他会看的。
一个星期后,他从房间里出来了。
他看起来,比之前更瘦了,但眼神,却不再那么冰冷。
他坐在我对面。
“我想见他们。”他说。
我的心,沉了下去。
该来的,总会来。
“好。”我说。
我再次拨通了那个香港的电话。
这一次,我表明了身份。
我说,我可能,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人。
对方的态度,立刻变得不一样了。
他们详细地询问了陈龙的年龄,我发现他的日期,还有那块玉佩的细节。
最后,他们说,会尽快派人过来核实。
两天后,一辆黑色的、气派的奔驰车,停在了我们小区的楼下。
从车上下来两个穿西装的男人,一个年纪大的,看起来很精明,另一个年轻的,跟在后面。
他们自我介绍,是霍家的律师和助理。
我把他们请进屋。
这是我们这个小破屋,第一次迎来这么“尊贵”的客人。
他们看到屋里的陈设,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但很快就掩饰过去了。
李娟给他们倒了水。
陈龙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当那个年长的律师看到陈龙的时候,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像,太像了。”他喃喃自语。
然后,他把目光,转向了我手中的那块玉佩。
我把玉佩递给他。
他从随身的公文包里,也拿出了一块玉佩。
那是一块凤形的玉佩。
他把两块玉佩,合在了一起。
龙凤呈祥,天衣无缝。
“错不了,是少爷。”
年轻的助理,激动地掏出手机,似乎要向谁汇报。
年长的律师,制止了他。
他转向陈龙,脸上露出了和蔼的、职业性的微笑。
“小少爷,我们,终于找到您了。”
陈龙面无表情。
“我老爷,您的爷爷,霍荆林先生,想见您。”
“您可以跟我们回香港吗?”
陈龙没有,他转过头,看着我。
他的眼神,让我读不懂。
“他的户口,还有身份证明,都在我这里。”我开口了。
“我需要确认,你们,能给他一个好的未来。”
年长的律师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陈先生,您放心。”
“霍家,是香港的名门望族。小少爷回去,自然是继承家业,前途无量。”
“我们霍家,也绝对不会亏待您这位恩人。”
他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这里是一张一百万的支票,是我们老爷的一点心意,感谢您这么多年,对小少爷的照顾。”
一百万。
1990年代末的一百万。
那是一个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我看着那张支票,突然觉得很可笑。
我十五年的含辛茹苦,我十五年的父子情深,在他们眼里,就值一百万?
我没有接。
“我不要钱。”我说。
“我只要他好。”
我转向陈龙。
“阿龙,你自己选。”
“你想跟他们走,我不拦着你。你是我儿子,我希望你有最好的前途。”
“你要是想留下……这个家,也永远是你的家。”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陈龙身上。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一个世纪都过去了。
然后,他走到了我面前。
他看着我,眼睛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复杂的情感。
“爸。”
他开口了。
这是他离家出走后,第一次,这么叫我。
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下来了。
“我想……去看看。”他说。
“看看那个本该属于我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
“但是,”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你看好了,我叫陈龙。我爸,叫陈明。”
“不管我以后变成什么样,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他又转向那两个律师。
“钱,你们拿回去。”
“这个人,”他指着我,“他是我爸。不是什么恩人。”
“你们霍家,欠他的,一辈子都还不清。”
说完,他回房间,简单地收拾了一个小包,就走了出来。
“走吧。”他对律师说。
他从我身边走过,没有再看我。
奔驰车开走了,带走了我的儿子。
我站在窗边,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路的尽头,久久没有动。
李娟从后面,抱住了我。
“他长大了,阿明。”
我手里,还攥着那张被我拒绝的支票。
不,我手里什么都没有。
我养了十五年的儿子,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变得空空荡荡。
家里突然就安静了下来。
我还是每天出车,拉货。
李娟还是每天,给我做好饭,等我回家。
我们谁也不提陈龙。
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想他。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了陈龙的电话。
是在香港打来的。
“喂,爸。”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哎。”我应了一声,喉咙发紧。
“我挺好的。”他说,“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像个城堡。有很多人伺候我。”
“爷爷……对我很好。”
“他们给我请了最好的老师,要教我很多东西。金融,管理,还有什么马术,高尔夫……”
他絮絮叨叨地说着。
我静静地听着。
“爸,我想你了。”他突然说。
我的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也是。”
“等我……等我把这边的事情理顺了,我就回去看你。看你和……李姨。”
“好。”
从那以后,他每个星期,都会给我打个电话。
我们聊他的新生活,聊我的工作。
聊李娟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
我们像一对最普通的父子。
半年后,他回来了。
他坐着那辆奔驰车,回到了我们那个小破屋。
他瘦了,也黑了,但整个人,气质完全变了。
他穿着我叫不出牌子的、剪裁合体的衣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眼神里,多了几分沉稳和锐利。
但他看到我,看到李娟,还是像个孩子一样,笑了起来。
“爸,李姨,我回来了。”
他给我们带了很多礼物。
贵重的,我连见都没见过的东西。
那天晚上,李娟做了一大桌子菜。
我们三个人,围在一起吃饭。
陈龙跟我讲他在香港的见闻。
讲那个大家族的复杂人际,讲商场的尔虞我诈。
他说,他不喜欢那里。
“太假了。”他说,“每个人都戴着面具。说话,做事,都要绕十八个弯。”
“还是咱们家好。”
他看着我和李娟,“简单,自在。”
我问他:“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他沉默了一下。
“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霍家那么大的产业,需要人来接手。”
“我是长子嫡孙,这是我的责任。”
我点了点头。
我懂。
“但是,”他又说,“我跟爷爷谈好了。”
“等我大学毕业,正式接管公司之后,我要把霍氏集团的内地总部,迁到深圳。”
我愣住了。
“为什么?”
他笑了。
“因为我爸在这里。”
“我的家,在这里。”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
他走的时候,从怀里,拿出了那块龙形玉佩。
“爸,这个,还是你替我保管吧。”
“它提醒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但它不能决定,我要到哪里去。”
我接过了玉佩。
这块曾经带给我无尽焦虑和恐惧的玉佩,在这一刻,我却觉得,它无比的温暖。
后来,李娟嫁给了我。
我们办了个简单的酒席,就在我们那个小区的院子里。
陈龙特地从香港赶回来,作为我们的证婚人。
他站在台上,拿着话筒,讲我们三个人的故事。
讲那个雨夜的天桥,讲那个铁皮屋,讲那辆蹬了不知多少里的三轮车。
讲着讲着,他哭了。
台下的我,和李娟,也哭了。
再后来,就像陈龙说的那样。
他大学毕业后,真的把霍氏的内地总部,搬到了深圳。
就在我们曾经住过的那个城中村附近。
那里,已经被夷为平地,建起了一座崭新的、气派的金融中心。
他成了那座大楼的总裁。
年轻有为,是深圳商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他把我和李娟,接到了市中心最好的小区,给我们买了套大房子。
他想让我退休,享清福。
我没同意。
我开了一辈子车,闲不下来。
我还在我的那个物流公司,当我的货车司机。
只是,我不再跑长途了。
每天,我开着车,穿梭在深圳的立交桥上。
路过那座我捡到陈龙的天桥时,我总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
桥还是那座桥。
但桥下的风景,早已物是人非。
深圳,这座城市,变得我快不认识了。
它那么新,那么快,那么繁华。
有时候,我会恍惚。
觉得过去的那些年,那些苦日子,都像是一场梦。
但每当我回到家,看到李娟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接到陈龙打来的电话,听到他叫我一声“爸”。
我就知道,那不是梦。
那是我陈明,用半辈子,换来的人生。
至于那块龙形玉佩。
它一直被我锁在保险柜里。
它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但我们的故事,还长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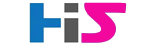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