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和情感冲突的故事开头。我们可以基于这个设定,构思一个更详细的故事:
---
"故事名称:" 《老班长的“骂”与“托”》
"人物:"
"我 (李明):" 年轻的销售代表,性格有些急躁,但关键时刻能扛事,和老班长关系很好。
"老班长 (王建国):" 原部队老班长,刚转业不久,性格耿直,讲义气,目前在一家公司担任重要职务或顾问。他在行业内有一定人脉和威望。
"领导 (张总):" 我所在公司的销售总监,精明强干,但对老班长非常忌惮和尊重。
"潜在客户 (某集团军司令):" 军方高层,身份尊贵,是八百万大单的关键决策者。
"故事梗概:"
我所在的科技公司,正全力争取一份高达八百万的军方智能化项目大单。这笔订单对我们公司意味着什么,不用我多说,全公司上下都在为此全力以赴。我作为项目的主要对接人之一,更是压力山大。
经过层层筛选和前期沟通,最终的销售谈判权落在了我和老班长头上。老班长虽然已不在部队,但在军方系统里的人脉和威望依然深厚,他经验丰富,说话分量足,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我满心欢喜地陪着老班长去见那位传说中要
相关阅读延伸:陪领导谈八百万大单,司令竟是我老班长,他当众骂我害惨他!
陪领导谈八百万大单,司令竟是我老班长,他当众骂我害惨他!
那声怒骂像炸雷般劈进会议室时,傅主任手里的茶杯碎了。
陶瓷片和着茶水溅到他锃亮的皮鞋上,他整个人僵在那儿,脸色白得像刷了层浆。
我看着他微微发抖的手指,又看向会议桌对面那个穿着笔挺军装的男人。
陈富贵。
我的老班长。
十五年没见了。
他胸前的资历章排得密密麻麻,肩章上的将星刺得我眼睛发酸。
他指着我,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弯曲,声音里压着滔天的怒意:“董瀚海!你小子害惨我了!”
满屋子寂静。
后勤部长于鑫垂着眼,傅主任的呼吸声又粗又急。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
八百万元的合同摊在桌上,墨迹还没干透。
01
凌晨两点,写字楼的灯还亮着三五盏。
我这层的,就剩我这一盏。
电脑屏幕的光映在脸上,有些发烫。
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发麻,又删掉几行。
方案已经改了第七版。
傅主任下午的话还在耳朵边嗡嗡响:“瀚海,这次不一样。军区换了个新司令,姓陈,作风硬得很。八百万的单子,够咱们部门吃两年。砸了,咱们集体卷铺盖。”他说这话时,没看我,盯着窗外,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西装袖口磨出的毛边。
我嗯了一声,继续翻手里那摞厚厚的技术参数。
有些数字,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
就跟当年背电台密码一样。
林思瑶给我端了杯浓茶进来,轻轻放在桌角。
小姑娘眼圈也是青的,跟着熬了好几天。
“董哥,后勤部那边刚发来补充要求,对防震等级又提了。”她把平板递过来,声音里透着倦意。
我接过来扫了几眼,心里算了算,成本又得上浮三个点。
得跟工厂那边再磨。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傅主任的消息:“确保万无一失。明天早上七点,公司楼下准时出发。”后面跟着三个感叹号。
我回了“收到”,把手机扣在桌上。
窗外的城市已经睡熟了,只有零星的灯光像困倦的眼睛。
我揉了揉太阳穴,端起那杯浓茶喝了一大口,苦涩的味道直冲脑门。
点开一个加密文件夹,里面是些旧照片。
手指划过屏幕,停在一张泛黄的合影上。
十几个晒得黝黑的年轻面孔,冲着镜头咧着嘴笑,背景是迷彩帐篷和飞扬的尘土。
站在中间那个,搂着我的肩膀,笑得见牙不见眼。
那时候他还不叫陈富贵,我们都叫他老陈,或者陈班长。
我关掉文件夹,把最后几页方案调整完。
保存,发送到傅主任邮箱。
关电脑的时候,主机风扇发出疲惫的嗡鸣。
我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上那块细微的裂纹。
明天要回“那里”去了。
虽然是以另一种身份。
心里某个角落,轻轻动了一下,说不清是期待,还是别的什么。
02
黑色轿车驶出市区,上了绕城高速。
傅主任坐在副驾驶,一路上嘴就没停过。
先是跟司机老周确认路线,接着又打电话给公司副总汇报行程,挂断后开始反复检查手里的公文包,拉链开了又合,合了又开。
里面装着最终版方案、公司资质、还有他特意准备的几盒高档茶叶。
“瀚海,”他忽然转过头看我,“你以前当过兵,对吧?”我正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绿化带出神,愣了一下才点头:“嗯,在野战部队待过几年。”傅主任像是找到了话题,身体侧过来一些:“那正好,部队里的事你熟。规矩啊,忌讳啊,多提醒我。这次对接的后勤部长姓于,听说是个笑面虎,不好对付。司令那边……”他顿了顿,压低声音,“我托人打听过,这位陈司令是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最恨花架子。汇报的时候,你多讲技术细节,实在的。客套话我来。”我点头说好。
车子继续往前开,渐渐远离城市楼群,远处露出青灰色的山脊轮廓。
越往前,路两旁的景色越熟悉。
虽然多了些新修的厂房和广告牌,但山形地势,错不了。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座椅边缘的皮革。
傅主任还在念叨:“……咱们厂的产品质量我绝对有信心,但军区采购,有时候不光是看质量。关系,人脉,都很关键。这个陈司令新官上任,肯定想烧几把火,咱们得让他这把火烧得顺心……”他的声音渐渐成了背景音。
我看见了那个岔路口。
左边是新修的柏油路,宽敞平坦,通往军区新大门。
右边是条旧路,窄一些,蜿蜒着伸向山坳深处。
那是我们当年拉练常走的路。
有一次夜间奔袭,就是在这条路上,我因为贪快抄近道,差点带偏了整个班。
老陈气得脸红脖子粗,当着全班的面对我吼:“董瀚海!你他娘的是不是觉得侦察兵就是耍小聪明?!”吼完了,还是他带着我重新摸回正确路线。
后来写检查,他陪我熬到后半夜。
车子拐上了左边的新路。
气派的门楼越来越近,哨兵持枪站得笔直。
傅主任整理了一下领带,又清了清嗓子。
我能听见他略重的呼吸声。
车子在哨卡前缓缓停下。
老周递上证件和预约函。
年轻的哨兵仔细核对,眼神锐利,动作一丝不苟。
我透过车窗,看着里面熟悉的训练场、营房楼,还有远处飘扬的旗帜。
风把旗子吹得猎猎作响。
十五年,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
又好像,一切都没变。
03
接待我们的是后勤部长于鑫。
五十岁上下,身材保持得很好,军装穿得板正。
他就在后勤部一楼的小会议室见我们,没去办公室。
握手时力度适中,脸上带着标准的笑容,但眼神里没什么温度。
“傅主任,董经理,坐。”他指了指会议桌对面的椅子,自己先坐下了。
勤务兵端来两杯白开水,轻轻放在我们面前。
没茶。
傅主任脸上笑容不变,从公文包里拿出方案,双手递过去:“于部长,这是我们为这次特种装备采购拟定的初步方案和报价,请您过目。”于鑫接过来,没急着翻,先放在桌上,手指点了点封面:“傅主任,你们公司的情况,我们有所了解。产品质量不错。”傅主任刚露出一点喜色,于鑫话锋一转:“但这次采购,司令亲自抓。他昨天开会还强调,要打破过去的供应商圈子,引入真正有实力、有担当的企业。不是质量达标就行,还得看综合保障能力,看长期合作的诚意。”他说得慢条斯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傅主任连连点头:“是是是,您说得对。我们公司绝对有诚意,保障能力您放心,我们在全国有十二个售后服务中心,响应时间……”于鑫抬手,做了个轻微下压的动作,打断了傅主任的话。
傅主任的声音戛然而止,脸上有点讪讪的。
于鑫这才翻开方案,快速浏览了几页。
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我注意到傅主任放在膝盖上的手,手指在轻微地互相摩挲。
这是他极度紧张时的小动作。
于鑫看了大约五分钟,合上方案。
“技术参数,我们后续会有专家团队详细评审。”他看向我,“董经理是技术负责人?”我点头:“是的,方案里大部分技术部分是我负责的。”于鑫打量了我一眼,那目光不像是在看一个企业经理,倒像是……在评估什么。
很短暂的一瞥。
“司令十点半有时间,可以给你们二十分钟。”他看了眼腕表,“还有四十分钟。你们在这里等吧。司令那边结束后,我再过来。”他说完就站起身,没有再多聊的意思。
傅主任赶紧也跟着站起来,想再说什么,于鑫已经转身出了会议室。
门轻轻合上。
傅主任站在原地,慢慢吐出一口长气,坐回椅子上,端起那杯白开水喝了一大口。
水已经凉了。
他扯了张纸巾,擦了擦额头。
其实那上面并没有汗。
“这位部长,不太好说话啊。”他低声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
我没接话,目光落在对面空着的椅子上。
刚才于鑫坐过的地方,军帽端端正正摆在桌角,帽檐朝着门口方向。
一丝不苟。
傅主任又拿起方案,重新翻看,嘴唇无声地翕动,像是在默诵重点。
窗外的阳光移了一点位置,照在会议桌光滑的表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斑。
远处隐约传来整齐的口号声,还有车辆驶过的低沉轰鸣。
这里的时间,仿佛走得比外面慢一些。
04
等待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
十点半过了,没有人来通知。
十点三刻,还是没动静。
傅主任坐不住了,站起来在不算宽敞的会议室里踱步。
走到窗边往外看,又走回来,看一眼手表。
表盘反射着细碎的光。
“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他看向我,眼神里带着询问,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我摇摇头:“可能前面会没开完。部队里常有的事。”其实我心里也有点打鼓。
二十分钟的汇报时间,本来就很紧张,再这么拖下去,恐怕真就只剩几句话的工夫了。
傅主任显然也想到了这点,眉头皱得更紧。
他走到门口,想开门看看,手放在门把上,又停住了。
不合适。
他收回手,整理了一下西装下摆,重新坐回椅子上,腰杆挺得笔直,像是准备随时起立。
又过了大概十分钟,走廊里终于传来脚步声。
但不是朝着会议室来的,是向着走廊另一头去了。
傅主任侧耳听着,脚步声渐渐远去。
他肩膀垮下来一点,轻轻叹了口气。
我也有些焦躁,目光在会议室里漫无目的地扫过。
陈设很简单,白墙,会议桌,椅子,墙角摆着饮水机和一盆绿植。
墙上挂着几幅字画,都是些励志标语和山水画。
我的视线掠过那些字画,停在办公桌后面墙上的一张照片上。
刚才于鑫坐那儿挡着,没看清。
现在他走了,那张镶在简单相框里的合影完全露了出来。
照片尺寸不大,里面人不少,像是很多年前的集体照。
穿着老式的军装,背景是简陋的营房。
我本来只是随意一瞥,可目光扫过照片中间那张年轻的脸时,心脏猛地一抽。
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呼吸都停了一瞬。
我站起身,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个动作。
傅主任疑惑地看向我。
我往前走了几步,靠近那张照片。
距离更近了,看得更清楚。
照片已经有些褪色,但那张脸,那双总是带着点不耐烦却又藏着笑意的眼睛,那个习惯性微微歪着头的姿势……错不了。
是陈富贵。
年轻了至少二十岁的陈富贵。
他站在第二排中间,搂着旁边一个战友的肩膀,笑得有点痞气。
而那个被他搂着的、笑得一脸傻气的年轻士兵……是我。
十七岁的我。
头发剃得短短的,脸上还带着没褪尽的稚气,因为笑得太开,眼睛眯成了缝。
我盯着照片,耳边嗡嗡作响。
时间好像在这一刻倒流,又好像凝固了。
我能闻到照片里似乎还残留着当年营房晒被子的阳光味,混着汗水和尘土的气息。
傅主任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瀚海?怎么了?”我没,也不了。
喉咙发紧。
手指冰凉。
照片下面有一行小字:“钢七连三班留念,1999年夏。”1999年。
整整十五年了。
门外的走廊里,再次传来脚步声。
这一次,沉稳,有力,越来越近。
停在会议室门外。
傅主任像弹簧一样从椅子上弹起来,迅速整理了一下领带和衣襟,脸上瞬间堆起职业化的、紧绷的笑容。
我的手心里,全是冷汗。
05
门被推开的时候,带进一股风。
不是穿堂风,是那种久居高位、步履生风带来的空气流动。
先走进来的是于鑫部长,他侧身让到一边,姿态恭敬。
然后,一个穿着夏季常服、肩扛将星的男人走了进来。
他个子不算特别高,但身板笔直,像一棵移动的松树。
脸庞比照片上宽了些,有了岁月的痕迹,肤色是长期户外活动留下的深麦色。
鬓角有些白了,但眉毛依然浓黑,眼神锐利,扫过来时,带着一种习惯性的审视。
傅主任立刻微微躬身,伸出双手:“陈司令,您好!我是腾飞科技的傅俊远,这位是我们技术部的董瀚海经理。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他的声音热情洋溢,语速很快。
陈司令的目光先落在傅主任身上,停留了大约一秒,略一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然后,他的视线很自然地移开,扫向我。
就在他目光触及我脸庞的那一瞬间,他整个人顿了一下。
非常细微的停顿,可能连半秒都不到。
但我和他都感觉到了。
他那双锐利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极快的、难以置信的愕然。
瞳孔微微收缩。
紧接着,那愕然被更复杂的情绪覆盖——惊讶、疑惑、还有某种被瞬间唤醒的、尘封已久的熟悉感。
他盯着我的脸,眉头慢慢蹙起,像是在记忆中急速搜索,核对。
傅主任的介绍词说完了,手还伸在空中。
陈司令没有去握他的手,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
于鑫部长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看看司令,又看看我,眼神里带着探究。
傅主任的手僵在那里,脸上的笑容开始发僵,他顺着陈司令的目光看向我,眼里满是疑惑和不安。
几秒钟的时间,被拉得无比漫长。
我能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
砰。
陈司令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下巴的线条绷紧了。
他向前走了一步,离我更近一些。
他身上有种淡淡的、混合着烟草和皂角的气味,很熟悉,又很陌生。
他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带着点沙哑,不是对着傅主任,而是直接冲着我:“你……”他停住了,又仔细看了我两眼,然后,像是终于确认了什么,那眼神里的情绪陡然变得激烈起来。
不是久别重逢的喜悦。
是压抑不住的怒意,是被猛然揭开的旧伤疤的刺痛,还有某种积郁多年、终于找到出口的爆发。
他抬起手,手指笔直地指向我的鼻子,因为用力,指尖微微发抖。
声音陡然拔高,像出膛的炮弹,炸响在安静的会议室里:“董瀚海!你小子害惨我了!”
06
“啪嚓!”清脆的碎裂声紧跟着炸响。
傅主任手里一直端着的、那杯已经凉透的白开水,连同杯子一起,脱手掉在了地上。
陶瓷碎片和水渍在他脚边溅开一片狼藉。
他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法,僵在原地,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眼睛瞪得老大,看看陈司令,又看看我,眼神里全是惊骇和绝望。
于鑫部长也明显吃了一惊,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表情,只是眉头蹙紧,目光在我和陈司令之间快速逡巡,带着审视和警惕。
会议室里死一般寂静。
只有空调出风口低沉的嗡嗡声,和傅主任粗重、颤抖的呼吸声。
我站在那里,迎着陈富贵——不,是陈司令——那几乎要喷出火的目光。
他胸口起伏着,手指还指着我,那根手指像一截标枪,钉死了我过去十五年的某一部分。
我脑子里有瞬间的空白,然后无数画面碎片一样涌上来:暴雨,泥泞,他背着我在山林里跋涉时的喘息和咒骂;团部办公室里,他站得笔直,替我承担大部分责任时紧抿的嘴角;宣布处分决定后,他拍着我肩膀说“滚蛋吧,别在这儿碍眼了”时发红的眼圈;还有退伍那天,他在站台远远看着,没过来,只是挥了挥手……“
司令,这……这……”傅主任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干涩,破碎,带着哭腔。
他向前挪了一小步,挡在我和陈司令之间一点点,虽然他自己也怕得厉害。
“司令,对不起,真对不起!董经理他……他年轻不懂事,要是以前有什么地方冒犯了您,我代他向您赔罪!这个项目……项目我们……”他语无伦次,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眼神哀求地看着陈司令,又回头狠狠瞪了我一眼,那意思是“你他妈的到底干了什么”。
陈司令根本没看他,他的目光越过傅主任颤抖的肩膀,死死钉在我脸上。
那眼神里的怒火在燃烧,但烧到深处,我好像又看到了一点别的,很复杂,我说不清。
于鑫部长上前一步,低声对陈司令说:“司令,您看这……”他想打个圆场,或者想请示如何处理。
陈司令猛地一挥手,打断了他。
动作幅度很大,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傅主任吓得往后一缩,差点踩到地上的碎片。
陈司令的胸膛剧烈起伏了一下,他深吸一口气,仿佛在强行压下翻腾的情绪。
然后,他转过头,对于鑫说,声音已经恢复了平稳,甚至有点过于平静:“合同呢?”
于鑫愣了一下:“合同?……在,在我办公室。”
陈司令点点头,命令道:“去拿过来。”
于鑫又是一愣,看了一眼面如死灰的傅主任,又看看我,迟疑道:“司令,这项目评审还没……”
陈司令重复了一遍,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去拿过来。现在。”
于鑫不再犹豫,立刻转身,快步走出了会议室。
门关上,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
傅主任的腿在发抖,他几乎要站不住了,用手撑着会议桌边缘。
他看着陈司令,眼神彻底绝望了。
他大概以为,司令是要当场撕毁合同,或者要亲自处理我这个“罪人”。
陈司令不再看我,他走到窗前,背对着我们,看着外面。
他的背影挺得笔直,但肩膀似乎微微塌下去一点。
阳光照在他的肩章上,将星冰冷地反着光。
傅主任凑到我耳边,用气声、咬牙切齿地说:“董瀚海……你……你把我害死了……”我没说话。
我看着陈富贵的背影。
十五年,他的背影宽厚了些,但那个轮廓,我认得。
07
于鑫很快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式几份的合同文本,还有钢笔。
他谨慎地将合同放在会议桌上,推到陈司令面前。
傅主任盯着那份合同,眼神像是看着即将宣判自己死刑的判决书。
陈司令转过身,走到桌边。
他没有坐下,就站着,拿起最上面那份合同。
他没有翻看前面密密麻麻的技术条款和商务条款,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乙方签章盖章的地方。
那里还空着。
于鑫适时地将拧开笔帽的钢笔递过去。
傅主任闭上了眼睛,仿佛不忍再看。
他觉得下一秒,司令就会把合同摔在他脸上,或者干脆撕碎。
陈司令接过笔,笔尖悬在签名栏上方,停了一秒。
然后,他手腕一动,笔尖落下。
不是愤怒的涂划,是流畅而有力的书写。
三个大字——“陈富贵”,跃然纸上。
笔锋刚劲,甚至有些凌厉,最后一笔重重顿下,几乎要划破纸背。
签完了。
他把笔搁在桌上,发出轻微的“咔哒”一声。
傅主任等了半天,没等到预想中的怒吼或碎裂声,他茫然地睁开眼睛。
当他看到陈司令已经签完字、将合同轻轻推过来的动作时,他的表情凝固了。
那是极度的震惊、茫然、不解混合在一起,让他那张平时精明的脸显得有点傻气。
他看看合同上新鲜的签名,又看看面无表情的陈司令,再看看我,嘴巴微微张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好像脑子被那声怒骂和这突如其来的签字搞短路了。
于鑫部长显然也极为意外,但他比傅主任镇定得多,只是眼底闪过深深的疑惑。
陈司令看着傅主任那副样子,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语气缓和了一些,公事公办地说:“傅主任,合同我签了。后续具体对接、技术细节、履约保障,你们和于部长按程序走。我只看结果。”
傅主任终于回过神,巨大的狂喜和后怕像潮水一样冲垮了他,他手忙脚乱地拿起合同,看着那个签名,确认了一遍又一遍,连声说:“谢谢司令!谢谢司令!您放心!我们一定……一定保证最好的结果!绝对不让您失望!”
他的手还在抖,合同纸被他捏得沙沙响。
陈司令没再理会他,目光重新转向我,那眼神里的怒火似乎平息了,但依然深沉,看不出情绪。
他对于鑫说:“于部长,你带傅主任去你办公室,把后续流程走一下。我跟……”他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跟董经理,单独聊几句。”
傅主任脸上的喜色瞬间又僵住了,他担心地看向我。
陈司令补充了一句:“关于合同里几个技术指标,我有些问题要问他。”这个理由很正当。
傅主任松了口气,但眼神里还是带着不安,他小声对我说:“瀚海,好好跟司令汇报,实事求是。”然后才跟着于鑫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门再次关上。
偌大的会议室里,只剩下我和陈富贵。
十五年后的重逢。
空气里还残留着刚才的硝烟味,和地上未干的水渍。
他指了指椅子:“坐。”自己先坐下了,坐在刚才于鑫坐的位置上。
我拉开他对面的椅子,坐下。
我们隔着一张光洁的会议桌,像谈判双方。
他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雾缓缓吐出,模糊了他的表情。
他透过烟雾看着我,看了很久,才开口,声音有些低沉:“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
08
烟雾在阳光里缓慢上升,扭动着消散。
他抽的烟还是当年那种牌子,劲儿大,味道冲。
熟悉的气味让时间的隔膜似乎薄了一些。
我没说话,等他继续说。
他弹了弹烟灰,目光落在我脸上,像是要找出这十五年留下的所有痕迹。
“退伍后,过得怎么样?”他问,语气很平常,像老友寒暄,如果忽略掉刚才那场风暴的话。
“还行。”我说,“跑过销售,干过安装,后来进了这家公司,混口饭吃。”他点点头,又吸了一口烟:“混口饭吃?混到能负责八百万军品项目的经理,你这口饭吃得不错。”这话听不出是褒是贬。
我沉默了一下,问:“你呢?怎么……当上司令了?”这话问出来,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恍惚。
当年那个因为文化底子薄、总被连长念叨“朽木”的老班长,成了肩上扛星的将军。
他咧了咧嘴,那笑容有点苦,又有点嘲弄的意味:“怎么当上的?托你小子的福啊。”烟灰积了长长一截,他忘了弹。
“那年,背了个处分。”他声音平缓下来,像在说别人的事,“本来板上钉钉的留队提干,黄了。心灰意冷,打报告想走了。老连长把我叫去,骂了一顿,说我熊包,一个处分就趴窝了?他问我,以后想就这么混日子,还是真想穿一辈子军装?”他顿了顿,把烟按灭在临时找来的烟灰缸(一个一次性纸杯)里,动作有点重。
“我想了一夜。然后,我找他要了复习资料。白天训练,晚上点着蜡烛看书。他妈的,比跑五十公里还累。字认识我,我不认识它。”他摇摇头,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痛苦。
“看了两年,考了三次。终于,上了军校。从最基础的学起。那时候我才知道,以前觉得自己在部队挺明白,其实狗屁不通。”他抬起眼,看着我,“你说,要不是你当年捅那个娄子,让我挨了处分,断了念想,我是不是还在那儿混着?是不是早就退伍回家,种地或者打工去了?”我喉咙发紧,不知道该说什么。
道歉?
现在听起来太苍白了。
那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
而我一直以为,我毁了他的前途。
“处分下来那天,我恨死你了。”他坦率地说,眼神锐利,“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完了。可后来,坐在军校教室里,听着那些我以前觉得是天书的课,我突然明白了。那一跤,摔得狠,但也把我摔醒了。不是那块料,硬赖着,才是真害人害己。走了另一条路,虽然苦,虽然绕,但可能,这才是适合我的路。”他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长长吐出一口气,好像把积压了多年的什么东西吐了出来。
“所以刚才骂你,是真想骂。那一嗓子,憋了十五年。每次想起当年那个憋屈劲儿,就想骂。”他看着我,眼神复杂,“但骂完了,也就完了。账,清了。”我低下头,看着桌面上的木纹。
胸口那块石头,没有消失,但好像挪开了一点,透进一丝气。
“刚才吓着你领导了。”他说,嘴角似乎弯了一下,但很快又平复,“那胖子,胆子不大。”我想起傅主任煞白的脸和摔碎的杯子,想笑,又笑不出来。
“项目的事,你放心。”他恢复了司令的语气,“公是公,私是私。你们的产品我了解过,确实符合要求。签字,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东西行。但你要记住,”他手指在桌上点了点,发出笃笃的轻响,“现在你不是我的兵,我也不是你班长。你是供应商,我是客户。该守的规矩,该有的标准,一点不能含糊。出了岔子,我照样翻脸不认人。明白吗?”
我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用力点头:“明白。”他看了我几秒,似乎想从我脸上确认这句话的分量。
然后,他站起身:“晚上别急着走。于部长安排了便饭,一起吃。有些话,饭桌上再说。”他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上,停住了,没回头,声音低了一些:“瀚海,能再见到你,挺好。”说完,拉开门走了出去。
我一个人坐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地上还有未干的水渍和碎瓷片。
阳光更斜了一些。
我抬手,摸了摸脸,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眼眶有点热。
09
晚饭安排在军区内部的一个小招待所餐厅,包厢不大,但干净整洁。
菜是家常菜,分量足,没有外面酒楼那些花哨的摆盘。
酒是普通的白酒,用军绿色搪瓷缸子装着。
傅主任下午跟于鑫办手续,大概听于鑫透露了点“陈司令和董经理是旧识”的风声,脸上的惊惶彻底褪去,换上了抑制不住的兴奋和红光。
他一再给陈司令敬酒,感谢的话说了一箩筐,姿态放得极低。
陈司令话不多,酒倒是喝得爽快,碰杯就干。
于鑫部长陪在一旁,话里话外也在试探我和司令的关系。
陈司令没多说,只简单提了句:“以前一个连队的,这小子是我带的兵。”傅主任恍然大悟状,看向我的眼神立刻不同了,多了几分热切和“你小子藏得深”的感慨。
酒过三巡,气氛活络了些。
陈司令脸上也有了点笑意,话渐渐多起来。
他不再提项目,也不提下午的冲突,开始讲些部队里的旧事,有些我知道,有些是我退伍后发生的。
傅主任和于鑫听得津津有味,不时附和。
陈司令说到兴起,端着缸子跟我碰了一下,然后手臂很自然地搭在我肩膀上,用力搂了搂。
这个动作,跟当年一模一样。
他带着酒气,凑近我耳边,声音不大,但桌上人都能听见:“这小子,当年是个刺儿头!脑子活,胆子贼大,就是不用在正道上!让他去摸对面蓝军的指挥所,他倒好,半路把人家炊事班的行军锅给顺回来了!说看看他们吃什么,判断战斗力!”桌上人都笑了起来。
傅主任笑得最大声。
我也笑了,想起那个灰头土脸背着口大黑锅回来的夜晚,被他骂得狗血淋头。
“还有一次,”陈司令眼睛发亮,像是彻底回到了过去,“野外生存训练,断粮三天。这小子,不知从哪儿摸到个马蜂窝,捅了下来,弄了一脸包,好歹搞了点蜂蜜。分的时候,自己就舔了舔沾手的,多的都给了班上体弱的兄弟。”
他拍了拍我的背,“傻不傻?”于鑫笑道:“这是战友情。”
傅主任连忙点头:“是啊是啊,重情义!”
陈司令喝了口酒,笑容慢慢淡下去,眼神变得深远:“部队里,一起吃过苦,挨过骂,趟过泥,滚过地,这种感情,外面人理解不了。有时候骂得最狠的,其实是把你当自己人,恨铁不成钢。”他说这话时,看着桌上的菜,又像是透过菜看到了别的什么。
傅主任若有所思。
陈司令转向傅主任,语气认真了些:“傅主任,项目给你们了,好好干。我骂他,是骂给我自己听的,也是骂给他听的。别因为过去那点事儿,或者现在这点关系,就放松了。东西不好,我第一个找他算账。”傅主任立刻正色道:“司令您放心!我们绝对百分之两百努力!”陈司令点点头,又端起缸子:“行了,不说工作了。今天高兴,喝酒!”那顿饭吃了很久。
陈司令讲了很多往事,有些我都快忘了,被他一件件翻出来。
傅主任彻底放松了,甚至开始跟于鑫聊起一些行业里的趣事。
包厢里烟雾缭绕,酒气蒸腾,充满了久违的、属于男人的、粗粝而直接的热闹。
散席时,陈司令已经有了七八分醉意,他握着我的手,用力摇了摇,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我的胳膊。
手掌宽厚,有力。
于鑫安排车送我们。
走出招待所,夜风一吹,酒醒了不少。
傅主任脚步有点飘,但脸上笑容就没断过。
他搂着我的肩膀,跟陈司令刚才的动作如出一辙,大着舌头说:“瀚海啊……董老弟!你可真是……真是我的福星!八百万!就这么……签了!回头……奖金!大大的!”我没说话,回头看了一眼。
招待所的灯光下,陈富贵还站在门口,于鑫陪在旁边。
他朝我们这边挥了挥手。
身影在灯光里,显得有些孤单,又异常挺拔。
10
回去的车里很安静。
傅主任上车没多久就睡着了,打着轻微的鼾声,嘴角还带着笑。
老周专注地开着车。
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沉入夜色的田野和远山。
路灯的光带连成一条流动的河,不断向后奔去。
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十五年前泥泞的山路和年轻的喝骂,一会儿是今天会议室里将星的闪光和那声雷霆般的怒吼,一会儿又是饭桌上他搂着我肩膀时掌心传来的温度。
还有那份签了字的合同。
八百万。
对我,对公司,是笔大单。
对他,可能只是一次正常的采购决策。
但他签下名字的那一瞬间,我知道,那不止是八百万。
那是十五年的时光,是一个命运的拐点,是一句未曾说出口的谅解,也是一种未曾改变的情谊。
车进了市区,灯火渐密。
傅主任醒了过来,揉了揉眼睛,看着窗外的霓虹,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坐直身体,清了清嗓子,声音已经恢复了平时的清晰,只是还带着点酒后的沙哑。
“瀚海。”他叫了一声。
我转过头看他。
车窗外的灯光在他脸上明明灭灭。
他斟酌着词句,慢慢说道:“今天……辛苦你了。”顿了一下,又说:“你和陈司令……以前的事,我不多问。那是你们的情分。”他看着我,眼神很认真,“这个项目,咱们一定得干漂亮。不能给你丢人,也不能……辜负了司令这份……公心。”他把“公心”两个字咬得有点重。
我点点头:“我明白,傅主任。”傅主任靠回座椅,望着前方,半晌,轻轻叹了口气,又像是笑了笑:“人情练达即文章啊……老话真有道理。”他停顿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又睡着了。
然后,他忽然侧过身,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
他的表情在昏暗的光线里有些模糊,但语气很清晰,带着点无奈,又有点如释重负的调侃:“但是瀚海,下次……再遇到这种‘老战友’,先给我透个底行不行?你傅哥我这心脏,经不起这么吓。”我愣了一下,看着他那张似乎一下午就熬出了些许憔悴,却又透着轻松的脸,终于也笑了笑,点点头:“好。”车子拐了个弯,驶向我们公司所在的那条路。
深夜的城市依然喧嚣,但又似乎离我们很远。
合同在公文包里,安安稳稳。
车窗外,灯火如海,无声流淌。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倾听,希望我的故事能给您们带来启发和思考。我是小郑说事,每天分享不一样的故事,期待您的关注。祝您阖家幸福!万事顺意!我们下期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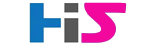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