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见深,明宪宗朱祁镇的儿子,明朝的第九位皇帝,他的太子生涯充满了波折和艰难,前后长达11年。这11年间,他经历了两次被废的危机,一次是被叔叔废,一次是差点被亲爹废,最终才艰难登基,成为明朝的皇帝。
"第一次被废:景泰八年(1457年)"
朱见深在宣德三年(1428年)被立为皇太子。然而,他的太子之位并没有一帆风顺。景泰三年(1452年),年仅25岁的明宣宗朱祁镇突然去世,朱见深年仅9岁,即位为皇帝,年号“景泰”。
由于朱见深年幼,朝政大权落到了他的叔叔——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英国公张辅,以及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手中。王振专权乱政,导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景泰七年(1456年),王振被处死,但朝政的混乱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景泰八年(1457年),发生了“夺门之变”。当时,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后,南明朝廷拥立了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帝,改元“景泰”。朱祁钰重用于谦等人,平定了“土木堡
相关内容:
太子,人家都以为是皇帝的儿子,天生坐拥半壁江山。但你要是朱见深,估计得天天做噩梦,梦见自己端着太子那碗饭,冷不丁就被人夺了碗,还得站在一边喝冷水。他第一次当太子,皇帝还不是亲爸爸,偏偏是叔叔朱祁钰。才当了没多久,叔叔一句话,他就没了“太子”的牌子,硬生生变成了个啥也不是的小孩。按理说,这戏剧性够了,但朱见深的太子路,后来拐得更玄乎。他爹归来,宝座又给他递上,可谁知道,这亲爹竟也差点再把儿子的太子帽摘了。

明朝那些年,皇家的事儿,真像大户人家过年串门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先说那一年,1449。北面瓦剌兵马乌压压的来,朱祁镇挺着身板,要亲自去打一场“面子仗”,还拉上一众文武和贵族子弟。儿子们在家里蹒跚学步,爹倒是英气风发,连皇宫里的石榴树都觉得今年风头带劲。
谁都想不到,好端端一出征,一个月,突然就传来消息:皇帝让人捉了,兵马玩儿了个团灭。京城里一下子炸了锅,老太后孙氏才是真有主意——不能让大明群龙无首,又不能真让瓦剌绑着皇帝挥舞大旗进城。她说,不管娃娃多大,得立个太子撑场面。于是两岁的朱见深,头顶太子印章,被摆上了台面,成了朝廷的“祥瑞”,实际什么都不懂,估计就多睡了一觉。

说来也巧,他叔叔朱祁钰——年纪不大,胆子不小,硬是被推上了监国的位置。外面瓦剌兵逼城下,朝内老臣围在一起下棋似的琢磨怎么守住北京。于谦、胡濙这些老狐狸自己也没少琢磨。如果是我们,估计也不敢拍胸脯说一定能守住命。
接下来又出了件“棘手事儿”。瓦剌可不傻,捉着皇帝回来敲门。守城的将士和大臣们那个纠结啊——开门吧,是叛国;不开吧,皇上还在门外,看着心里拧巴。更别说孙太后和朱祁钰了,谁都知道怎么做才合规矩,可这世道哪有那么清清楚楚的“规矩”?于是朱祁钰,托大臣、用点小心思,在一片议论和没头苍蝇中登上了宝座。

但这个局面看着怪异。朱祁钰其实有亲儿子朱见济,按大家伙心里话说,对亲侄子朱见深有点“膈应”。孩子大了,该想自己儿子能接班。正经王八经的朝廷,也怕乱了宗法,所以太子和皇帝关系变得滑稽起来——叔叔当国,侄子做太子,亲儿子拍边坐。就像饭桌上,夹菜给邻家孩子,亲儿子只能望碗兴叹。
这里插个嘴,小地方的古老戏班子演“易储”那出,总有个坏人怂恿皇帝,给宫人送金银,收买人心。朱祁钰干的也是这路数:赏赐大臣黄金银子,想拉拢他们把自己儿子抬上去,背地里和太监使眼色。你说,贿赂这种事,做皇帝的还真用得上,而且也真见效。于是太子朱见深就这么被“挤下来了”,成了个闲置“沂王”,在宫里落寞地陪着老太后。亲生老爸远在南宫,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儿子的心也冷了半截。

时间一晃五年,又一个夜黑风高的日子,朱祁镇病重,局势突然一变,他自己搞了个“夺门之变”——皇位抢回来,朱见深也翻身回到太子椅子上。你以为接下来就能风平浪静?别着急。
其实这爹和儿子七年没怎么见着面,感情鬆散得很。朱见深真正的亲情归属,全在奶奶孙太后身边。而这时候,他妈周氏又给家里添了一道难题。周贵妃仗着自己生了长子,托人去和老太后传话,说皇后钱氏无子还残疾,不配母仪天下。朱祁镇那脾气,听了更是火冒三丈,直接把太监骂走,皇后地位不动摇,周氏只能忍着做贵妃。

这场后妃争斗,看表皮是女人在斗,其实后面就是跟太子之位比拼。朱祁镇多年风浪,没了单纯心气,多了不少猜疑。他甚至开始琢磨,要不要重新换太子,让钱皇后收养的二儿子朱见潾当接班人——小儿子虽然不是亲生,但好歹能给钱氏一个“子凭母贵”的名分。
你看看,这一家子,权谋和亲情搅成了麻花。朱见深夹在重重算计和父亲的冷漠之中,说不出话也没人听。他那些日子,多半是无声的难过,凡是有点供奉的人,都知道看父皇脸色行事,遇风使舵。

真要说这局面最后一锤定音,还是李贤这老臣。朱祁镇病榻边问他,要不要废太子,李贤一头叩门连磕,不让动,死活撑着,他说太子才是宗社的命脉。说话有分量,关键时刻捏住了局面。朱祁镇这一犹豫,也就放过了朱见深。你说,孩子在大病父亲面前痛哭,抱着腿哭成个泪人,场面像极了隔壁家小子被爹打——不是不心疼,是心疼得发慌。
最后,朱祁镇走了,朱见深顺顺当当做了皇帝。其实算下来,太子这顶帽子,他戴了11年,丢了又捡,捡了又怕丢。明朝几百年,也只有他这牛劲——被废过还真能再捡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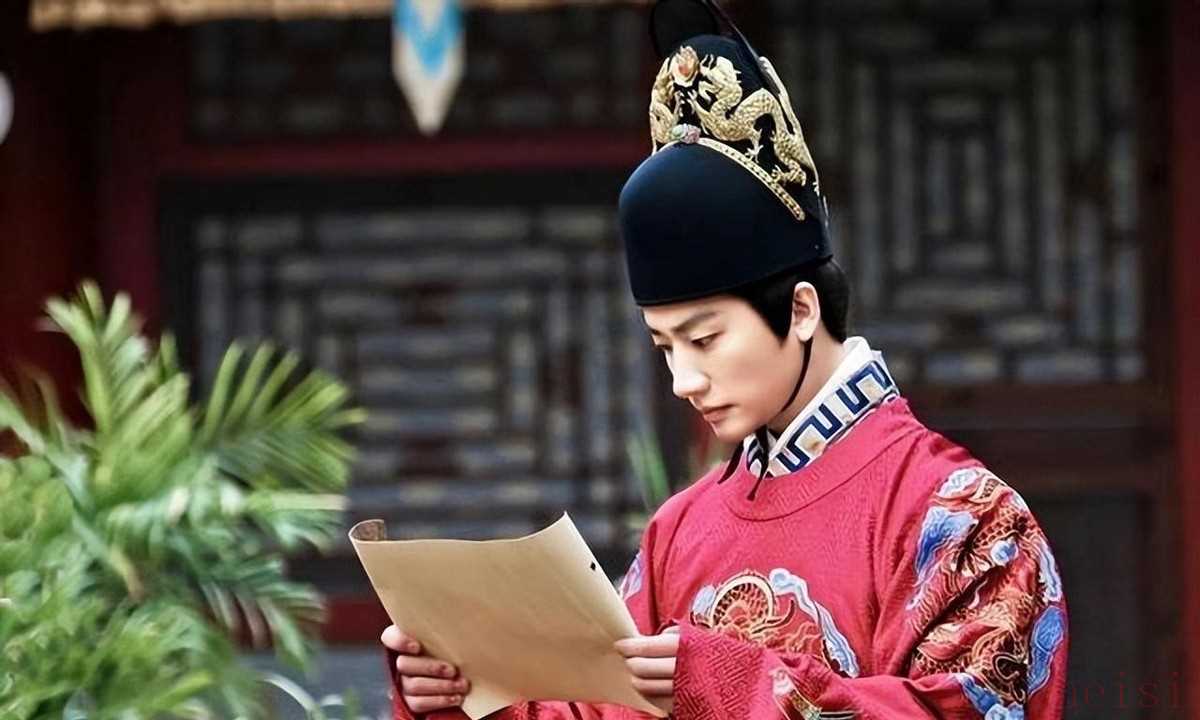
但你要说,这童年能没点影响吗?朱见深从头到尾都活在那种不确信、不被信任中。长大成人,他最信赖的,居然是个自小在身边的宫女万贞儿。十八岁少年做皇帝,对身边的女人,偏执又依赖,万贞儿年长他十七岁,还被他捧成贵妃。一生挚爱,说到底,是他心里从来就没安全感。
后来,万贞儿的孩子早夭,她自己也老了。朱见深却没有变心,反而更倚赖她。这份感情,大明宫里议论纷纷,史书也留了话——等到万贞儿走了,朱见深心灰意冷,说“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果不其然,半年后,他也跟着走了。

你品一品,这不是普通的追爱故事。是灾乱与亲情博弈里的余流,是少年太子畏惧失去,被权利和摇摆的父爱砸打出来的那种深情。宫里的月儿,外面的风,权谋与人性,最后都化到这句“我亦将去矣”里了。
想想如今,谁还会相信,皇家的太子日子能难到这个份上?老话常说“贵人多磨”,但朱见深这一路磨得太近人心了。你觉得,如果不是那一堆捉摸不定的亲情和风浪,他还能有后来的痴恋和深情吗?这段故事,留下的问号,也许比任何朝代的太子都多。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