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个非常生动且具有时代特色的个人经历分享!80年代,尤其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选择工作单位(“挑单位”)往往直接关系到未来的生活轨迹和“差距”。
你和你同学的选择,以及后来的“差距巨大”,反映了几个可能的时代背景和个人选择因素:
1. "行业吸引力与福利待遇":
"烟厂":在那个年代,烟草行业通常被认为是“铁饭碗”单位之一,福利待遇相对较好,工作稳定,收入可能高于一般工厂。同时,烟厂可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被认为是“吃皇粮”的。
"副食厂":生产食品,虽然也是生活必需品,但可能面临着生产条件、管理、效益等方面的挑战,福利待遇和稳定性可能不如烟厂。也可能工作环境(如油烟味)相对较差。
2. "个人偏好与价值观":
"你的同学":选择副食厂,显然更看重工作环境,厌恶烟味,这反映了她对生活品质和健康有更高的要求,或者更倾向于与食品这种“干净”行业打交道。
"你":选择了烟厂,可能更看重单位提供的稳定性和潜在的经济回报,或者当时没有特别在意烟味,或者认为烟厂的工作机会更难得。
3. "时代背景下的“差距”":
"经济回报":改革开放初期,不同行业的经济效益差异
相关内容:
01 铁饭碗与糖纸
1981年的夏天,空气里弥漫着槐花和焦灼混合的气味。我和林欣然,两个刚从技校毕业的女孩,并肩站在地区劳动局的红榜前,像两只等待被命运分拣的小兽。
红榜上,铅字打印的单位名称,每一个都像一枚沉甸甸的勋章。排在最前面的,是市卷烟厂。那四个字黑体加粗,仿佛自带金光。我爹在家念叨了一周:“晓雯,要是能进烟厂,咱家祖坟都算冒青烟了。那是‘天字第一号’的铁饭zhan碗。”
我攥着衣角,心脏怦怦直跳。卷烟厂,意味着高福利、福利分房、别人挤破头都拿不到的“内部烟票”,更意味着一种工人阶级贵族的身份。我能感觉到身边所有人投来的艳羡目光,那目光像一件华美的袍子,我渴望能穿上它。
“晓雯,你看,”欣然捅了捅我,她指着红榜靠下的位置,“市副食品厂。这个好,离我家近。”
我顺着她白皙的手指看去,那几个字小了一号,挤在一堆酱油厂、纺织厂的名字中间,显得有些灰头土脸。我皱了皱眉:“副食品厂?整天跟酱醋糖纸打交道,有什么出息。”
欣然的鼻子可爱地皱了一下,她压低声音,凑到我耳边:“我可不去烟厂,上次路过,那股烟草味儿齁得我三天吃不下饭。我怕闻那个。”
我愣住了。在“铁饭碗”的光芒面前,“怕烟味”这种理由,听起来像糖纸一样轻飘、不值一提。我看着欣然清澈的眼睛,那里面没有对未来的深谋遠慮,只有少女最直接的喜恶。
轮到我们做选择时,几乎没有犹豫。
我挺起胸膛,用尽量洪亮的声音报出:“徐晓雯,选择市卷烟厂。”负责登记的干部抬起眼皮,赞许地点点头,仿佛在我的档案上盖下了一个“优等”的戳。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被一台精密的国家机器设定好了最优航线。
接着是林欣然,她轻快地说:“林欣然,我去副食品厂。”
干部愣了一下,似乎想劝她什么,但看着她一脸“欣然”的样子,终究只是撇撇嘴,笔尖在纸上划过。
走出劳动局,夏日的阳光刺眼。我感觉自己走在一条金光大道上,而欣然,她选择了一条不起眼的林荫小道。我心里既有对她“傻气”的惋惜,也有一丝无法言说的优越感。
“欣然,你可想好了,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我忍不住最后劝她。
她买了根冰棍,咬得嘎嘣脆,满不在乎地笑:“一辈子那么长,谁知道呢?起码我上班不用捏着鼻子。走了晓雯,改天去我们厂里找我,我给你拿处理的碎糖块!”
她骑着自行车,像只轻快的蝴蝶,消失在街角。我看着手里的报到证,那上面的油墨香混合着我对未来的想象,压过了空气中所有的槐花香。我告诉自己,我选择的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堡垒,而欣然选择的,不过是一间漏风的糖果屋。我们人生的差距,从这个夏天就已经注定。
进厂的第一天,那股浓郁、甜腻又呛人的烟草烘烤味,像一堵墙一样拍在我脸上。车间里,巨大的卷烟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穿着蓝色工服的老师傅们,表情严肃,动作精准。我被分配到包装车间,每天的工作,就是将一包包印着“金葉”牌的香烟装入条盒。那红与金的包装,摸上去有一种权力的质感。
每个月,我最期待的就是发工资和福利。厚厚的信封,里面不仅有比欣然高出一大截的工资,还有几张珍贵的烟票和各种工业券。逢年过节,厂里发的福利更是堆成小山。我妈每次都会把印着“市卷菸廠”字样的福利袋子,故意放在院子里最显眼的位置。
有一次,我拿着刚发的两张自行车票,去找欣然。她正在厂里的小卖部帮工,身上一股子酸梅粉的味道。她们厂刚进了一批处理的布料,她正兴致勃勃地盘算着给自己做条新裙子。
“欣然,看,自行车票!”我扬了扬手里的票,像个炫耀战利品的将军。
她眼睛亮了一下,真心为我高兴:“太好了晓雯!凤凰牌的?”
“那当然。”我矜持地点点头。
她搓了搓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还在攒钱呢。我们厂效益一般,奖金少。不过也还好,我们主任说,最近厂里在琢磨搞承包,说不定以后能多赚点。”
“承包?”我不太懂这个词,但直觉上觉得那是一种不稳定的东西。我拍拍她的肩膀,语重心长:“你们厂就是花样多,不像我们,稳当。欣然,要不找找关系,看能不能调到我们厂来?守仓库也比你那儿强。”
欣然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算了,我还是喜欢我这儿,每天闻着都甜丝丝的。”
我看着她满足的样子,摇了摇头。她不懂,生活的甜,不是靠糖纸的气味来定义的,而是靠“铁饭碗”的重量来压秤的。那时候的我坚信,我手里的自行车票,比她那一屋子的糖纸加起来都重。

02 寂静的轰鸣
九十年代的风,是从窗户缝里钻进来的,起初只是一丝凉意,后来就变成了卷走一切的呼啸。
卷烟厂那震耳欲聋的轰鸣,是我听了十年的背景音。我早已习惯了在巨大的噪音里和工友们打着手势交流,习惯了那股烟草味像第二层皮肤一样包裹着自己。这座工厂,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我在这里从小徐熬成了徐姐,从流水线女工做到了车间小组长,并在三年前,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福利房。拿到钥匙那天,我请欣然来家里吃饭,她带来的礼物是一袋她们厂自己产的大白兔奶糖。
“晓雯,你这日子,真是稳当。”欣然抚摸着刷着白漆的墙壁,由衷地感叹。彼时,她的副食品厂早已被一家私人老板承包,老员工要么买断工龄回家,要么拿着微薄的工资留下。欣然选择了留下,她说老板人不错,让她管着销售,虽然累,但每月都能拿提成,比以前挣得多。
我给她夹了一筷子红烧肉,心里那份优越感依旧坚固:“那是,我们是国家的大儿子,饿不着。”
可“大儿子”也会生病。
变化是悄无声息开始的。先是外省的香烟牌子,包装越来越花哨,味道也更“柔和”,悄悄占领了街角的烟纸店。“金葉”牌的销量开始下滑。接着,是厂里的奖金,从厚厚的一沓变成薄薄几张。再后来,一些老旧的机器开始停转,车间里出现了空旷的角落,曾经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第一次出现了间歇。
那轰鸣的间歇,像心脏漏跳了一拍,让所有人都感到心慌。
工友们开始窃窃私语,讨论着谁家的亲戚在南方开了工厂,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大家谈论的,都是“离开”的事情。而我们这些四十岁上下、把青春都献给了烟厂的人,又能离开去哪里呢?我们的“价格标签”——烟厂职工,曾经是荣耀,现在却像一个沉重的烙印,把我们钉死在这里。
2001年,厂里进行“优化减员”,其实就是裁员。名单公布那天,整个厂区一片死寂。我最好的徒弟,一个才二十五岁的小姑娘,哭着来找我,她的名字在名单上。我去找车间主任,那个曾经在我面前点头哈腰的男人,第一次对我板起了脸:“徐姐,这是厂里的决定,我也没办法。现在效益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座我依赖了二十年的堡垒,墙壁上已经布满了裂痕。
由于我是老员工和小组长,侥幸留了下来,但被调到了一个叫“档案科”的地方。这是厂里有名的“西伯利亚”,专门安置那些没处去、又不能开除的老员工。一同被调去的,还有几个老技术员和图书管理员。
档案科在办公楼最角落的地下室,阴冷潮湿,空气里弥漫着纸张发霉的味道。这里堆满了从建厂以来的各种文件、图纸、报表和照片。我的工作,就是整理这些故纸堆。
巨大的失落感攫住了我。从一个管理者,变成一个无人问津的档案员,我的“价格标签”仿佛一夜之间被撕掉了一大半。刚开始的几个月,我每天都坐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前发呆,耳边总能幻听到车间那熟悉的轰鸣。可一回神,四周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一天下午,我无意中翻开一个蒙着厚厚灰尘的牛皮纸袋,里面掉出几张泛黄的香烟包装纸。那不是我们熟悉的“金葉”牌,而是一种叫“雙喜”的牌子,设计得极为典雅,上面印着一对穿着民国服饰的新人,图案细腻,色彩古朴。生产日期写着:民國二十六年。
我愣住了。原来我们厂的前身,是一家创立于三十年代的私营烟草公司。
这个发现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我从未窥见过的大门。我开始疯狂地、系统地翻阅那些被遗忘的档案。我像是着了魔,每天第一個到,最后一个走,小心翼翼地用软布擦去那些旧照片上的灰尘,用胶水修复破损的文献。
我读到了工厂的创始人,一位留洋归来的实业家,他如何引进德国设备,如何亲自设计商标;我看到了一张张黑白照片,上面是穿着长衫的老师傅,用精湛的手工技艺筛选烟叶;我甚至找到了一本手写的工艺手册,详细记录了“雙喜”牌香烟独特的“二次回酵”工艺,那是为了让口感更醇和的秘方,早已失传。
这些故事、这些细节,像一块块碎片,在我手中拼接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工厂形象。它不再是那台冰冷、轰鸣的国家机器,而是一个有过温度、有过梦想、有过灵魂的生命体。
地下室里没有窗户,我却仿佛看到了光。当厂里最后一台卷烟机也停止轰鸣,当最后一批工人办理完离岗手续,当整座工厂彻底陷入死寂时,我的心里,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轰鸣声,正变得越来越响亮。

03 你那儿,还好吗?
2003年的冬天,格外冷。厂里只剩下几十个像我一样留守的人员,每月领着几百块的生活费。偌大的厂区,荒草长得比人还高。红砖墙的缝隙里,钻出了倔强的绿色。曾经象征着荣耀的“市卷烟厂”几个鎏金大字,也剥落得不成样子。
那天我爸生日,我取了300块钱,想去商场给他买件羊毛衫。路过市中心最繁华的百货大楼,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进去。我知道里面的价格,不是我能承受的。我在街边徘徊,最后走进了一家折扣店。
就在我翻检着一堆处理毛衣时,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晓雯?”
我回头,看见了林欣然。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她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米色羊绒大衣,脖子上系着一条雅致的丝巾,手里拎着几个看起来就很昂贵的购物袋。她的头发烫成了时髦的卷发,化着淡妆,整个人容光焕发。
而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厂棉服,脚上是笨重的劳保鞋,头发随便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脸上是长期不见阳光的蜡黄。我们站在一堆打折商品中间,像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
“欣然……”我局促地把手插进口袋里,感觉自己像个被当场抓获的小偷。
她惊喜地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她的手温暖而柔软。“真的是你!哎呀,多少年没见了!你……你这是?”她的目光落在我手边的处理毛衣上,随即又迅速移开,装作什么都没看到。
“我……给我爸买件衣服。”我 stammered, my face burning.
“走走走,别在这儿看了,我知道有家店的男装特别好,我刚给我爸也买了一件,我带你去。”她不由分说地拉起我,朝我刚才不敢进去的百货大楼走去。
我像个木偶一样被她拖着。走进温暖明亮、飘着香水味的商场,我感觉自己身上的寒酸气味与这里格格不入。欣然熟门熟路地带着我上到三楼男装区,指着一件挂在橱窗里的羊绒衫说:“你看这个怎么样?颜色稳重,料子也好。”
我瞥了一眼价签,四个数字让我心跳都漏了一拍。
“太……太贵了。”我小声说。
欣然好像没听见,她把导购叫过来,让她取下那件衣服。“你爸穿着肯定好看。来,包起来。”她说着就从钱包里抽出一张卡。
“别!欣然,这不行!”我急忙按住她的手。
“哎呀,同学一场,客气什么!就当是我送给叔叔的生日礼物。”她笑得爽朗,但那笑容在我看来,却像一根针,精准地刺入我最脆弱的自尊。
我执意不肯,她拗不过我,只好作罢。气氛一时有些尴尬。我们走到商场的咖啡厅,她点了两杯昂贵的咖啡。我捧着那杯热气腾ü腾的卡布奇诺,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
沉默了一会儿,她终于开口,小心翼翼地问:“晓雯,你们厂……现在怎么样了?我听说,好像停产了?”
就是这个问题。
一个简单、客观、甚至带着关切的问句,却像一颗子弹,瞬间击碎了我用二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所有骄傲和壁垒。
是啊,怎么样了?停产了,倒闭了,成了一片废墟。而我,这个当年选择了“天字第一号”铁饭碗的徐晓wen,现在连给父亲买一件体面毛衣的钱都拿不出。而她,那个当年因为“怕烟味”而选择糖果屋的林欣ran,现在却可以云淡风轻地在这里消费。
我所有的坚持、所有的隐忍、所有的优越感,在这一刻,都成了一个巨大的笑话。
我低下头,看着咖啡杯里那颗用巧克力粉画出的心形图案,它慢慢地、慢慢地融化,模糊成一团。我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一滴,两滴,砸进奶泡里,无声无息。
“我……我被分到档案室了。”我哽咽着说出这句话,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欣然沉默了。她伸过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没有怜悯,没有炫耀,只是一种复杂的、带着温度的理解。
“晓雯,”她轻声说,“我那个副食品厂,十年前就没了。老板把我留下来,是因为我会盘点,会算账。后来我自己出来单干,最开始就在街边摆摊卖袜子,一天下来脚都站肿了。没什么稳当不稳当的,都是自己熬出来的。”
我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她。我一直以为,她是选择了安逸,而我是选择了荣耀。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们只是在命运的分岔路口,被推上了两条不同的传送带。我的传送带曾经平稳高速,却在半途戛然而止。而她的传送带,从一开始就颠簸崎岖,却逼着她学会了奔跑。
那天告别时,欣然执意塞给我一个信封,说是借我的。我没有拒绝。我需要那笔钱,不仅是为了给父亲买件像样的礼物,更是为了买回我那点所剩无几的、面对生活的勇气。
走在回家的路上,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握着那个信封,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那个靠一张“价格标签”就能定义人生价值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而我,必须亲手为自己的人生,重新做一个标价。

04 撕掉价格标签
回到那个阴冷的地下档案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整理出的所有关于工厂历史的资料——那些泛黄的照片、脆弱的文献、手写的工艺手册——全部摊开在桌子上。
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群沉睡的证人。
欣然的话,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 clinging to 的最后一丝幻想。我不能再守着这片废墟,等待着某个虚无缥缈的“政策”来拯救我。我必须自己寻找出路。
出路在哪里?
我的目光落在那张民國二十六年的“雙喜”牌香烟包装纸上。那对穿着喜服的新人,在昏暗的灯光下,笑容依然灿烂。我忽然想起了我那位当历史老师的父亲。他总说:“任何事物,一旦有了时间,就有了价值。怕就怕,你只看到它现在的样子,看不到它过去的样子。”
过去的样子……
一个疯狂的念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沌的脑海。
这座工厂最大的价值,或许不是那些已经生锈的机器,也不是这片可以卖给开发商的土地,而是它那被遗忘的、长达七十年的历史!这些档案,这些故事,这些工艺,才是它最珍贵的“隐形资产”。
我们不能把它当废铁卖掉!我们应该把它变成一座博物馆,一个能讲述城市记忆的地方!
这个念头让我浑身燥热,血液奔流。我立刻开始动笔。我不知道该写给谁,也不知道写出来的东西有没有用,我只知道我必须把它写下来。
我给这份东西起名为《关于将市卷烟厂旧址改造为工业遗产文化公园的提案》。
我把自己关在档案室里,没日没yè地写。我把工厂的创建史、品牌的发展史、工艺的变迁史, meticulously 地整理出来。我把我找到的那些老照片一张张翻拍,附在提案后面。我甚至画出了蹩脚的规划图:这里可以做博物馆,展示老机器和旧商标;那里可以做创意工坊,租给年轻的设计师;那片空地,可以做露天剧场……
我父亲成了我唯一的读者。他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地看我的草稿。他不懂什么叫“文化公园”,但他看懂了里面的故事。他指着那本手写的工艺手册,对我说:“晓雯,这个‘二次回酵’,你得写清楚。这不是技术,这是‘匠心’。现在的人,就缺这个。”
“匠心”这个词,像火种一样点亮了我。是啊,这不是一堆冷冰冰的机器和厂房,这是一个关于匠心、关于创造、关于一个城市几代人记忆的故事。
提案写了整整一个月,修改了十几遍,厚得像一块砖头。我把它打印出来,第一站就去了厂里留守处。主任是个快退休的老干部,他翻了几页,就把提案推了回来,像在掸掉一个麻烦。
“徐晓雯,你是不是闲糊涂了?搞博物馆?谁给你钱?现在厂里连水电费都快交不起了!我告诉你,市里已经跟宏达地产谈得差不多了,这块地卖掉,给大伙儿补发点安置费,就谢天谢地了。你别在这儿瞎折腾了!”
我碰了一鼻子灰,但没有放弃。我拿着提案,开始往市里的各个部门跑。规划局、经委、宣传部……我像一个祥林嫂,一遍遍地讲述着我的“故事”。大多数时候,我连负责人的面都见不到,就被门口的保安或者年轻的办事员打发了。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疯子。
那段时间,我花光了欣然给我的钱,每天只啃两个馒头。我被人嘲笑,被人驱赶,但我心里那团火,却越烧越旺。因为我知道,我不再是为了一份工资、一个“饭碗”在战斗。我在为那些沉睡的档案,为那些黑白照片上沉默的工匠,为这座工厂被遗忘的灵魂在战斗。
我是在撕掉那个外界贴给它,也贴给我的“破产工厂”、“下岗女工”的价格标签,我要亲手为它,也为我自己,赋予新的价值。
转机出现在我去市文化局的第十次。之前九次,我都被前台拦住了。第十次,我抱着那摞沉重的提案,决定就在大厅里等。从早上八点,一直等到下午五点下班。就在我准备离开时,一个年轻人叫住了我。
“您是……徐晓雯女士吧?”他看起来三十出Tóu,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我姓张,是局里的。我听前台说了您好几次了。您的提案,能让我看看吗?”
我把那份已经被我翻得卷了边的提案递给他,心情忐忑。
他站着,就在人来人往的大厅里,一页一页,看得极其认真。他的眉头时而舒展,时而紧锁。看了足足半个小时,他抬起头,眼睛里闪着一种我从未在别人眼中看到过的光芒。
“徐女士,”他扶了扶眼镜,语气激动,“您知道吗?我们市正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缺一个有分量的、能代表本市近代工业发展的项目。您这个提案……来得太是时候了!”

05 一包香烟的分量
项目评审会,被安排在市政府的小礼堂里。气氛庄严肃穆。
台下坐着市里的主要领导,以及银行和投资方的代表。我的对手,是财大气粗的宏达地产。他们的代表,一个油头粉面的年轻人,正在台上用PPT展示着他们的宏伟蓝图。
屏幕上,精美的3D效果图不断切换。我们那片破败的厂区,在他们的规划里,将变成一个叫“金色罗马”的高档住宅小区。欧式风格的建筑,气派的喷泉花园,闪闪发光的玻璃幕墙。每一张图,都仿佛在宣告着它未来的不菲售价。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年轻代表用激昂的语调做着总结,“我们将投资五个亿,将这片没落的工业废墟,打造成我市新的商业地标和高档生活区!预计三年内,就能为市里带来超过两个亿的税收!”
台下响起一阵压抑的赞叹声。所有人都被那串巨大的数字吸引了。“五个亿”、“两个亿”,这些词像重锤一样,敲在每个人的心上。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标签”。
接下来,轮到我了。
我穿着连夜从欣然那里借来的一套得体的灰色套装,走上了台。我没有准备PPT,因为我买不起投影仪,也不会用。我的手里,只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我走到演讲台前,深深鞠了一躬。台下静悄悄的,许多人的目光里带着同情和不耐烦。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螳臂当车,一场注定失败的表演。
我没有说话,而是从文件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几样东西,放在了老式的投影仪上。那是一种能把实物投影到幕布上的设备。
第一件东西,是那张民國二十六年的“雙喜”牌香烟包装纸。
幕布上,那对笑容灿烂的民国新人,瞬间被放大了几十倍,清晰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各位领导,”我的声音有些发颤,但我努力让它保持平稳,“这包烟,诞生于1937年。它的制造商,就是我们卷烟厂的前身。它的设计师,是工厂的创始人,一位叫叶景清的先生。他希望这款烟,能为战乱中的中国人,带去一点喜气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接着,我放上了第二件东西:一张工人的黑白合影。
“这是1952年,公私合营后的第一张全家福。照片上这些朴实的工人,用他们的双手,让工厂的产量翻了十倍,我们的‘金葉’牌香烟,就是从他们手里诞生的,曾经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骄傲。”
然后是第三件,第四件……我把我从档案里找到的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老照片、老图纸、老报纸,一件件地展示出来。我没有讲空洞的理论,也没有谈宏大的规划,我只是在讲故事。
讲那个叫叶景清的创始人,如何为了“二次回酵”的口感,在闷热的工房里实验了三个月;讲那个叫李师傅的老技术员,如何靠耳朵就能听出机器哪里出了故障;讲包装车间的女工们,如何在枯燥的流水线上,梦想着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大学……
我讲到我自己,一个十八岁进厂,把整个青春都献给这座工厂的普通女工。我讲它曾经的轰鸣如何让我安心,又讲它后来的寂静如何让我心碎。
“宏达地产的方案很好,它告诉我们这片土地值多少钱。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我的声音大了起来,目光扫过台下每一个人,“一个城市的记忆,值多少钱?一代人的匠心,值多少钱?我们父辈的青春和汗水,又值多少钱?”
“这些东西,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它是一座城市的根。如果把它铲平,盖成一栋栋没有记忆的水泥房子,那我们斩断的,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文脉!”
“我的方案,不承诺几个亿的税收。我只能承诺,我会把这座工厂,变成一个活着的博物馆。让我们的孩子,能在这里看到爷爷奶奶们曾经如何奋斗;让外来的游客,能在这里读懂我们这座城市的性格。我承诺,我会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创意孵化器’,让那些有梦想但没钱的年轻人,能在这里租一个廉价的工位,开始他们的创业之路。这,是一种新的‘创造’,一种能生长出未来的投资!”
我的演讲结束了。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素的情感。我把那包珍藏的、已经空了的“雙喜”牌香烟盒,轻轻放在演讲台上。
“这就是我的全部计划。它的分量,就在这一包香煙里。”
我说完,再次鞠躬。
全场一片寂静。长达半分钟的寂静。
然后,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的市委书记,缓缓地带头鼓起了掌。那掌声,起初稀疏,随即变得雷鸣般响亮。我看到文化局的小张站了起来,用力地鼓掌,眼圈泛红。我甚至看到银行的代表,也露出了思索和赞许的神情。
在那震耳欲聋的掌声中,我泪流满面。我知道,我赢了。不是赢了宏达地产,而是赢回了这座工厂的尊严,也赢回了我自己的尊严。

06 把烟抽成了云
五年后,初夏。
曾经荒草丛生的卷烟厂,脱胎换骨。红砖墙被清洗干净,爬满了青翠的藤蔓。高大的烟囱不再冒烟,而被彩绘成了一支巨大的“铅笔”,直插云霄。这里被正式命名为“1937文创园”。
我陪着几位来访的记者,走在园区里。空气中,不再是呛人的烟草味,而是混合着咖啡香、书墨香和青草的气息。
曾经轰鸣的生产车间,变成了挑高巨大的美术馆,正在展出一位年轻艺术家的装置艺术。包装车间,被改造成一个个独立的玻璃工作室,里面坐着服装设计师、陶艺家、程序员……他们专注的神情,让我想起了当年流水线上的工友。
地下档案室被完整保留,升级成了园区的文献中心,由我亲自管理。而那台曾经决定了我和欣然命运的、锈迹斑斑的卷烟机,如今安静地陈列在工厂博物馆的正中央,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展品。孩子们好奇地抚摸着它冰冷的金属外壳,听我讲述它曾经的故事。
我的身份,是“1937文创园”的首席文化顾问。这是一个我自己创造的岗位。我不再需要任何外部的“价格标签”来定义我。我的价值,就写在这园区的每一块砖、每一寸草地上。
园区里最火爆的地方,是一家名叫“欣然”的咖啡馆。它开在原来的厂长办公室,有一个可以俯瞰整个园区的露台。老板,自然是林欣然。
那天下午,送走记者,我来到咖啡馆的露台上找她。她正在吧台后忙碌,指挥着年轻的店员。看到我,她 smilingly 端来一杯手冲咖啡。
“徐大顾问,今天又接待了什么大人物?”她打趣我。
“别取笑了。”我接过咖啡,抿了一口,香醇浓郁。我们并肩靠在栏杆上,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有写生的美院学生,有牵手散步的情侣,有带着孩子来参观的家庭。阳光透过梧桐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一切都那么宁静而美好。
“晓雯,你知道吗?”欣然忽然开口,“有时候我真觉得像做梦一样。二十多年前,我最怕的就是你身上的烟味。每次你从厂里出来,我都躲着你走。”
我笑了:“我知道。那时候我觉得你傻,为了躲点味道,放弃那么好的铁饭碗。”
“现在看来,是我傻。”她摇摇头,目光悠远,“我只是单纯地跑开了,为了自己舒服。而你,你留了下来,最后却把所有人都讨厌的‘烟’,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美丽的‘云’。”
我愣住了。她的话,像一句诗,轻轻地,却精准地击中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是啊,我叫晓雯。晨晓的晓,云纹的雯。仿佛冥冥中自有注定。我用了半生的时间,守着一片呛人的浓烟,最后,却亲手将它升华为了一片绚烂的云霞。
欣然的咖啡馆,成了园区里许多创业者的“会议室”。她利用自己多年经商的人脉,为这些年轻人牵线搭桥,介绍客户。她的“糖果屋”,以一种新的方式,在这个我构建的“温室”里,继续散发着甜美的香气。
我们不再是两条 perging 的人生轨迹。我们,以及园区里的所有人,都成为了这个新生生態系统里,互相依存、共生共荣的一部分。
“对了,”欣然想起什么,从吧台拿出一个精致的礼盒递给我,“给你。我们厂……哦不,我们公司的新产品,白巧克力做的‘雙喜’牌,复刻了你博物馆里那个民国版的样子。”
我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块块洁白的巧克力,上面印着那对笑容灿爛的民国新人。
我拿起一块,放入口中。甜而不腻,入口即化。
我看着远方,城市的天际线在夕阳下泛着金光。我想起了1981年那个燥热的夏天,那个站在红榜前,对未来充满幻想又无比迷茫的自己。我终于可以跨越二十多年的时光,与那个年轻的女孩和解。
我告诉她:别怕。你选的那条路,起初烟雾弥漫,但只要你坚持走下去,穿过浓烟,就能看到最美的云。最好的反击,不是毁灭,而是创造。最好的价值,不是被赋予,而是被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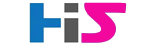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