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描述了一种关于红塔山香烟的怀旧和批判性观点。以下是对这段话的解读:
1. "90年代烟民首选":这句话表明在90年代,红塔山香烟在中国市场上非常受欢迎,被许多烟民视为首选。这可能是因为它的品牌知名度、口感或者其他因素。
2. "香味醇厚红塔山":这句话强调了红塔山香烟的口感和香味,描述为醇厚,暗示了其独特的烟草风味。
3. "现十块一包":这句话提到了红塔山香烟的当前价格,即每包10元。这可能与通货膨胀、市场供需变化或其他经济因素有关。
4. "褚时健:难辞其咎":这句话提到了褚时健,前红塔山集团董事长。褚时健因其商业成就和争议性行为而闻名。这里的“难辞其咎”可能指的是褚时健在红塔山发展过程中的决策或行为对香烟的受欢迎程度和当前价格产生了影响。
总的来说,这段话通过描述红塔山香烟在90年代的受欢迎程度、口感、当前价格以及与褚时健的关系,表达了一种怀旧和批判性的情感。它可能反映了人们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同时也对当前的经济和市场状况有所暗示。
相关内容:
红塔山的烟与人心:褚时健的起落

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烟,从酒桌上被当成“面子”的硬通货,掉到了小卖部柜台里十块钱随手拎走的那一层?这不是“市场有点波动”的程度,这是时代拐了个急弯。绕来绕去,拐点上站着一个人——褚时健,他把红塔山推上去,也亲眼看着它往下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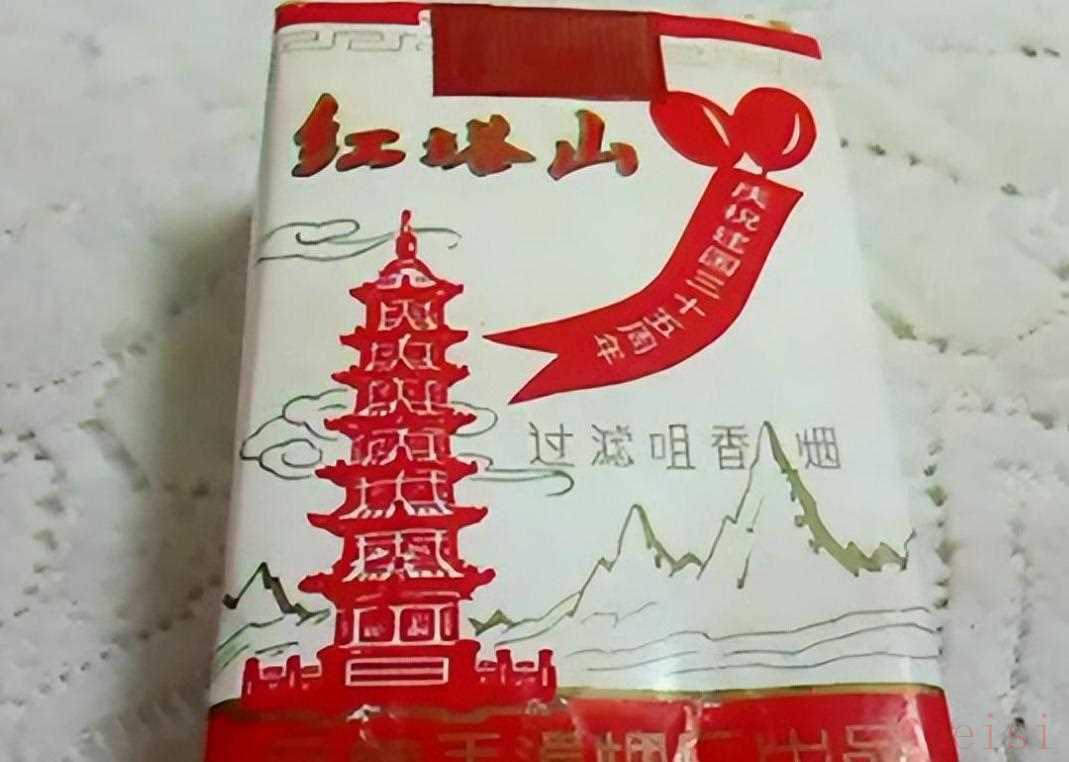
先说那阵风光。九十年代的中国,钱和机会在空气里,都带着火药味儿。玉溪的小厂子,靠着一茬又一茬的技改、扩产,像打了鸡血一样往外长。车间的灯不关,工人两班倒,夜里三点进去还能看见电焊火花在墙上跳。烟丝的味儿和机油味混在一起,门口的货车排队到转角,尾灯红一串,跟过年似的热闹。
有人把这家厂的变化总结成几组数字:厂房、设备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家底,从几千万元一路堆到七十亿;看不见却更值钱的那口碑和名头,被评给了三百三十多亿的价儿。听上去像玄学,可你问当年的经销商,谁没在“红塔山”三个字上碰过好运气?

那会儿的生产线一刻不敢松,烟支像子弹一样刷刷刷往外吐。账本上算得特别明白:做一条成本就那么几块钱,出厂价就翻了好几层楼。到了批发商手里,运过路、打一圈招呼,贴上“紧俏”两个字,零售一条敢卖两百。最妙的是,这戏不是一地一处在演,全国小城大城一个腔调:柜台后面堆得像砖头,柜台前面排队各有各的眼神。
这种火爆不是天上掉的,是有人拿着尺子和笔去划分“谁有,谁没有”。褚时健坐在那个位置,话有分量,签字更是金口玉言。一张条子批下来,这个季度谁能多拿几条,谁能切一块好地盘,心里都明白。外头人跑玉溪见他,带的礼不敢轻,话也不敢多,茶几上的烟灰缸里永远半碗灰。闲话一句,那些年,生意场上很多规矩就是这么磨出来的。

权力跟生意一搅和,边界就模糊了。厂家有计划,市场有饥饿感,中间的缝隙里,自然长出油水。某些人能用“内线”的价格拿到货,再以“市场”的价格转出去,赚的是天大的差价。你问谁在中间打点,答案不难猜。一次两次,收益大得吓人,谁能不心动?褚时健太懂供求,他也太懂人心。
转折来的时候,不是雷声,是一封信。1995年的初春,河南三门峡寄来一封没署名的举报,把一堆人带进了灯光更亮的房间。信里说得不含糊:批条怎么走,账往哪边挪,谁拿了什么样的好处。后面的事情就像你能想到的那样,一支队伍进驻,翻账本、查转账、看电话记录。有人说数字是最不会说谎的,这话一点不玄。银行流水上一笔一笔往外冒,打在纸上,跟青天白日一样明目张胆。

调查往深里拧,情况就越来越难看。被挖出来的不只是现金——收来送去的名表、珠宝、画轴,盒子都还在,编号齐整。更扎眼的是那些数额:用“批烟倒烟”的方式吃进来的好处,有人民币三千六百多万,还有港币一百万、美金三十万;另外挪用的公款,折成美金,是一百七十多万。数字摆那儿,没法狡赖。到了后来,褚时健从厂门口消失了,他进了另一个有铁门和哨兵的地方。人们在茶馆里小声议论,更多的人装作不知道,继续忙自己的日子。这也是常态。
没有哪家大厂子扛得住这种地震。褚时健走了,位置不能空着。昆明那边来了一位副市长出身的干部,字国瑞,顶上火线。他一落座,迎面就是一屋子复杂的眼神:有把他当救火队的,有把他当外人,还有干脆在心里盘算盘算“老子要不要另谋出路”的。更麻烦的,是红塔山的名声已经伤了筋骨,外头经销商嘴上不说,心里在打鼓:这货以后还好不?

字国瑞手里拿的是新算盘。他想着不能只盯着卷烟这一个篮子,万一再出事呢?于是,往外投,往侧边拓,想搭出一个“多点开花”的格局。想法不算坏,现实却给人上课得很快——陌生行业里你连路口都不知道在哪儿,花出去的钱像石子扔进水潭,咕咚一下就没了回响。主业还在,地位也还在,但心思分了身,刀尖就不那么锋利了。
再说市场外头。你停下来喘,别人正好开始sprint。比如“杭烟”,人家就认准了一个道理:把烟做好,把牌子讲明白。一波一波地打广告、调口感、做包装,甚至琢磨从一支烟里讲出年轻、时髦、讲究的故事。红塔山这边呢?还摆着老架势,觉得“我这香气、我这底子,谁不认?”可时代变了,饭局上换了人,柜台前站的是另一代。

其实坏苗头早就冒头了。很多跑市场的业务员,仗着货紧,口气也紧。以前是人家求你,现在是你挑人。讲价的时候脑袋一扬,爱搭不理。谁受得了?批发商也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对面品牌的人倒了杯热茶,问问家里情况,价格也诚意,慢慢地,货就往那边走了。等反过神来,你发现原来的“铁粉”不在电话簿第一页了。这事儿不惊天,但很致命。
进入二十一世纪,变得快的不只手机。广告从电视转到网络,年轻人不再认老故事,卫生政策也收紧,城市里禁烟的红线画得到处都是。高端烟的盘子还在,但规矩更严、口味更挑。到2010年前后,红塔山在高端这一块的份额缩到一个难看的数字,差不多只剩下二个百分点。你能怪谁?别人天天迭代,今天讲工艺,明天说品味,后天上明星,连盒子都做出了设计感;你这边还在一遍遍复唱“我们曾经谁谁谁抽我们”。历史是好听,钱袋子不听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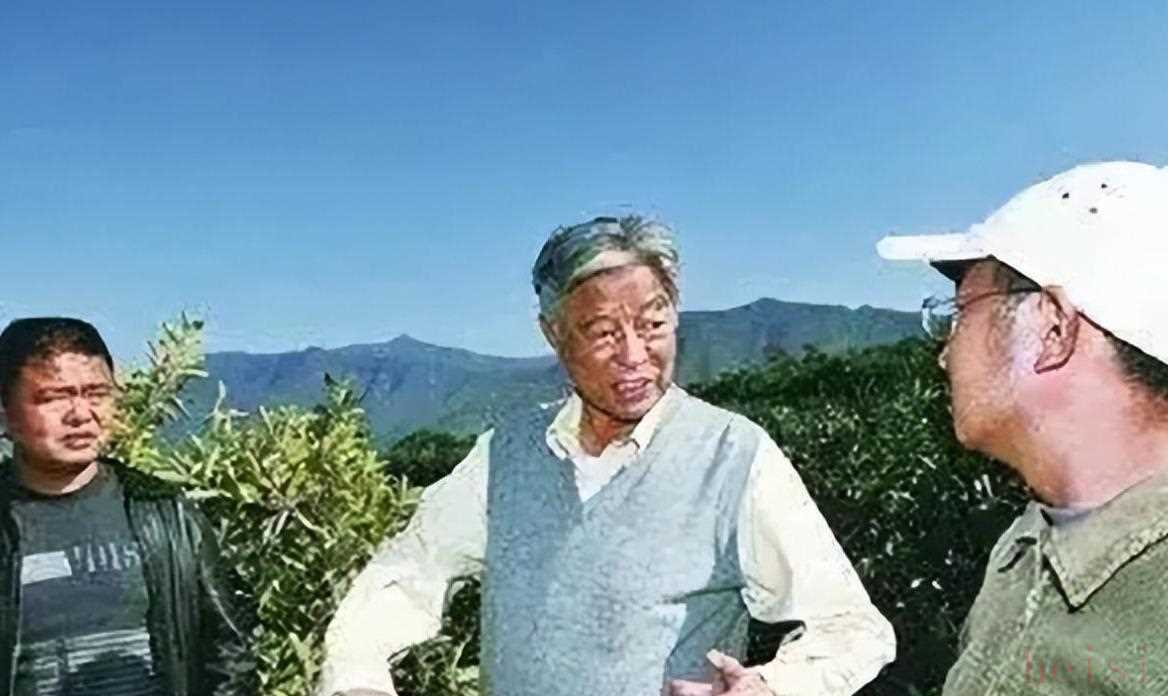
说句实在话,红塔山不是没挣扎。尝试过出新品,想过走年轻化,可一步慢步步慢。广告投放还用老法子,渠道关系还是老面孔,最要命的,是内心深处那点“我们不需要低头”的劲儿。等到销售数据实在不好看了,采取了最直观的一招——降价。十几块一包的烟,给压到了十块钱档,销量回来了些,但牌子的层次也一起下去了。你在街角烟酒店能看到它的身影,买的人也不少,只是再也不是当年饭局上那种“递过去就能让局面亮一下”的东西了。
我记得在一个云贵小镇的烟酒行,老板娘一边给顾客找零,一边跟我嘀咕:“红塔山啊,现在靠老主顾,年轻人更喜欢新包装、新味道的,说起来也怪。”怪不怪,很难一句话说清。有一部分是世界变快了,有一部分是我们变慢了,还有一部分,是当年留下的那点骄傲和侥幸,拖了很久的后腿。

把镜头拉回褚时健。他是天才的经营者,也是活得很像我们身边人的那种老企业家——果断、要强、相信人情的力量,也难免在权力和利益的缝里打了滑。后来他在云南种橙子,许多人说那是赎罪,也有人说那是重来一次。不做评判。只是你看那片橙林,觉得人这一辈子,起落之间,最怕的是把握不住“如何在顺境里收住手”。
红塔山的路,成就过一个时代的消费记忆,也照出了企业最容易犯的错:把“别人愿意买”当成了“永远会买”。市场对谁都公平,今天捧你,明天就能把你按在地上摩擦。更何况,它不只看口碑,也看姿态、看诚意、看你是不是还在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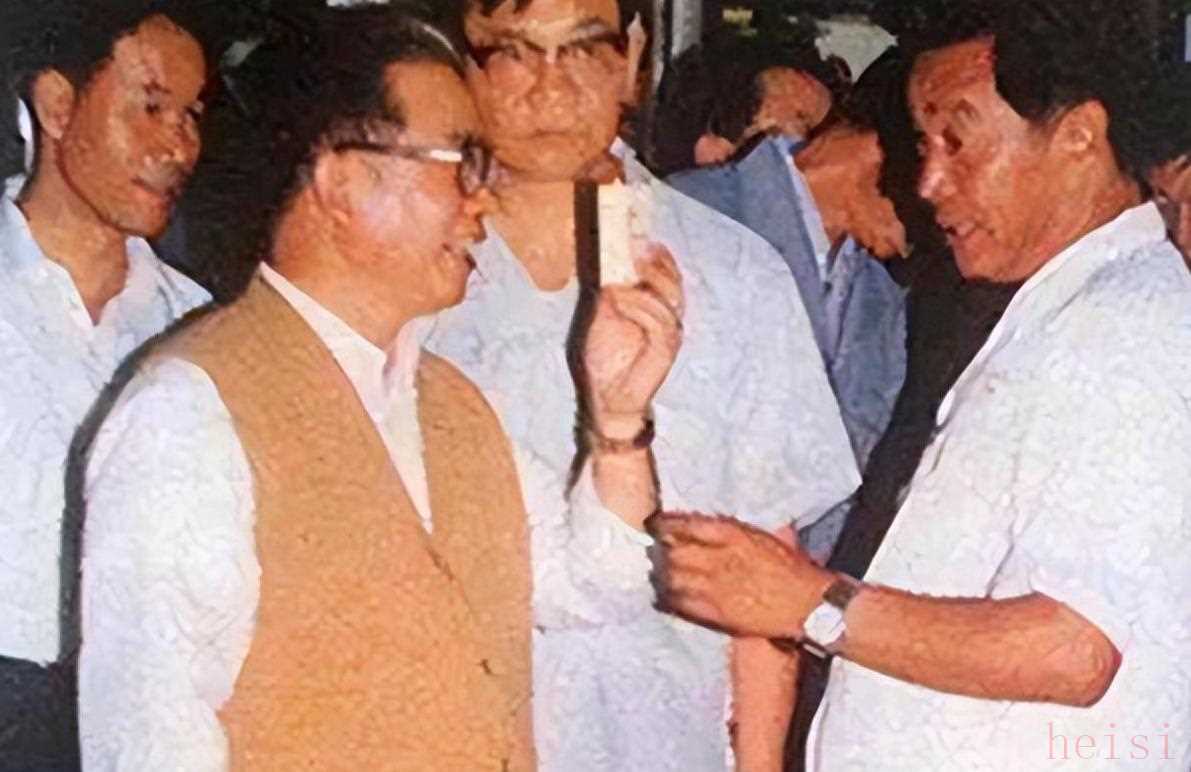
写到这里,我们不必急着下结论。红塔山会不会再回来?也许吧,品牌的生命有时比人长,老树也可能发新芽。可另一个问题更难:如果当年某些批条少批一笔,如果某些业务员多一次微笑,如果在巅峰时刻稍微放低一点头,后来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疼?这问题问给红塔山,也问给每个以为自己“稳了”的人。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